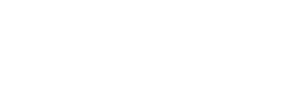大城市之死:纽约不属于人民

【作者简介】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自由记者,毕业于汉普郡学院和纽约大学新闻研究院,为《卫报》(Guardia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新共和》(New Republic)、《连线》(Wired)、《石板》(Slate)等多家媒体供稿。曾任职于美国半岛电视台。现居纽约。
2016年,我哥哥和他太太及3岁的小孩被告知他们得搬离威廉斯堡的公寓。他们已经在那儿住了12年,那间小巧又租金尚可的公寓,即将被转建成公寓大楼,价格他们负担不起。他们隔壁邻居刚好是我的前男友,也被通知得搬出他一房一厅的公寓,管委会给他30天搬家。他现在在纽约到处跟人家分租房子,一边试着寻找预算内可以长待的容身之处。几个月后,因为我很担心自己会遇到类似的状况,便试着搞清楚我住的公寓的租金涨幅有没有受到管制。我向州法院提出申请,接着州政府通知房东,后来房东决定在对他有利的情况下不会涨房租。现在我的租金是月缴,一边等待州政府最后的决议,这可能会花上几年的时间。我哥哥一家、我前男友和我都是中产阶级,住在这城市非常不容易。
差不多同时,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和地方新闻电台“纽约一号”(New York 1)合作的调查发现,65%的纽约人很担心接下来几年会因为房价水涨船高而被迫搬迁。这份研究的发现关系到经济和种族,低收入家庭、拉丁裔、黑人更容易担心涨房租,但其实每个人都很焦虑自己就是下一个被开刀的对象,甚至连那些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住房危机。
假如中产阶级甚至一些高收入的人都负担不了纽约的房租,工人阶级和穷人又该怎么办?我哥哥和嫂嫂很幸运,能住得起更贵的房子,即便他们得节衣缩食才能继续待在纽约。我也很弹性,我年轻,有钱,还不会太快结婚,我可以搞得定。其他人就只有一种选择:反击。
布什维克区的谢弗街(Schaefer Street)有一栋三层楼的塑料外墙建筑。10年前,移居者根本不会考虑搬进此区;5年前开始,有些人开始搬进来,所谓的“打头阵”吧。即使犯罪率高,街道肮脏,但这里仍然算是还不错的区域,离地铁L线只有几条街,L线直直通往威廉斯堡的贝德福德大道(Bedford Avenue),然后再到曼哈顿。谢弗街绿树成荫,邻近公园,安静,对面是学校,附近有很多停车位。缙绅化从西边开始侵蚀(布什维克区的单人房平均租金已经涨到2150美元),就像街区里的其他建筑一样,这栋建筑物也是大规模迫迁的显眼目标。差别只是它的租客不愿离开。
事情从夏日某天的一张通知单开始,每个租户的门下都被塞了一张。“这栋建筑物已经被拍卖了,”通知单上说,“请把租金转给以下住址。”36岁的凯伦·吉内塔(Karen Genetta)立刻知道自己面临战斗。吉内塔是这栋建筑物内倒数第二个搬来的,在通知单来到之前,已经在此住了8年。这栋建筑物简直一团糟—走道残破不堪,前门还不能上锁—但租金非常便宜,1000美元就能租到两个房间,每六间公寓里就有一间的租金是稳定的,法律规定了每年的涨幅。1969年之前盖的建筑物,凡是有六间以上公寓的,多半都受租金管制保障,但那并没有让房东停手把布什维克数百间公寓大楼的人赶走。虽然没有太多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人从受租金管制的楼房被赶出去,但只要沿着布什维克散步一圈,就会知道为数不少:看看布鲁克林正在改头换面的老房子,就能猜到租户是被非法强迫驱离的。有时候房东会用5000、1万、5万或甚至10万美元向租户收购,接受收购的租户并不知道这笔钱多快会蒸发,假设一个受租金管制的建筑物月租金是800美元,而市场行情是2000美元,5万美元只能让你在新公寓住上几年。虽说这笔钱对勉强过活的人来说,感觉似乎已经很多。
这个案例里,钱并不重要,因为这群租户知道在此时的纽约,就算他们离开,也不会有地方可去。他们以前的房东很恼人,很少维修和打扫房子,常常很晚收租,但吉内塔和邻居忍耐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很值,如果大楼被卖掉,那一切都会变的。
然后,那张通知单无预警地出现在门下。很快就有两个男人出现在大楼里自我介绍,接着冲进吉内塔的公寓说要看她的房间。她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评估每间公寓究竟值多少钱,但其他事情她就不知道了:这两个男人告诉她自己的名字,但他们的公司没有网站,也没说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几个礼拜以后,从这两个男人的“有限责任公司”(LLC)来了正式的表格,一张说所有租户都需要重新申请各自的公寓,另一张则宣称每间公寓都欠租7000美元。故事发展到这里,通常不知道自己应有权益的租户,就会开始离开。但这栋建筑物里一个住户联系了地方上有几十年历史的非营利组织里奇伍德布什维克长者理事会(Ridgewood Bushwick Senior Citizens Council, RBSCC),最近雇请了更多律师来抗议迫迁。
这栋建筑的租户开始着手准备文件—租金收据,历年来的汇票、租约。他们开始以电子邮件来跟踪和共享新房东的种种骚扰手段。某一周他们发现这栋大楼的垃圾被弃置在对街,他们怀疑房东指使管理员这么做,目的是为了让住户跟卫生署(Department of Sanitation)杠上;另一次他们发现大楼的监视器不是对向通道而是对着每户人家的门口。这群住户开始把所有的情报转知给里奇伍德布什维克长者理事会。他们采取的行动很单纯,但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会做的程度。房东买下受租金管制的楼房,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大部分时候有办法把人赶走。当下一次新房东又来电时,吉内塔已经准备好了。
“我跟他们说,你们还要从我这边要什么的话,直接打给我律师,跟他谈,”她说,“然后他就哑口无言了。”
吉内塔和她的邻居们并非运动分子,纯粹只是因为没有退路,为了要留在家园,得起身捍卫自己。吉内塔有个房地产业的朋友,一直都在带顾客看对街的房子,格局类似,一个月租金2500美元。他们知道这是纽约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但吉内塔和她的先生雅各布很幸运:他们没有小孩,雅各布有份稳定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很弹性(吉内塔从事电子商务),有办法搬去德国柏林,雅各布的公司在那边,柏林的租金管制法更成熟。而其他住户并没有后路。
琳恩和伦赛住在2L公寓25年了;雷在这栋大楼里长大;海迪·马丁内斯(Heidi Martinez)住在楼上,她的生活因为事件的发展而压力日渐沉重,但她还是留下了。海迪现在38岁,她就在附近的谢弗街长大。
“我记得很清楚我5岁、6岁、7岁、8岁、9岁的时候,车行驶在布什维克大道,置身在这些楼房之间,”海迪告诉我,“当时感觉就好像在第三世界国家。”
海迪一家四处搬来搬去,最后落脚在布朗克斯。6年前,当她要为自己和高中的儿子找间公寓,她找到了谢弗街这栋大楼。当时和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语,海迪还记得玄关处总有人在赌博,还有一股杂草的气味。她搬进去的第一周听见门外有人,从孔隙向屋外望,看到几个人从大楼屋顶沿着梯子爬下,手上握着枪,非常吓人。到现在,她知道邻居不停换人,所以她试着采取行动。她拿到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开始跟一家地方公司合作,兼职带顾客看公寓。刚开始这份工作进展缓慢,但突然间似乎出现很多人要申请她带看的每间公寓。她服务的公司告诉她不要接受任何申请,除非那个人的年收入是月租金的40倍。
“我拒绝了好几百人,”她说,“我想要给他们方便,弄到自己要抓狂了。”
她开始频繁听说收购的事情,她的公司要她载一位房子被收购的老太太四处转转寻找新公寓,但她找不到合意的。某天海迪意识到,同样的状况已经逼近到家门口了。她一个人在家,听见门廊的窸窣声,她望向屋顶下方的梯子,看见几个男人爬下来,这次是不动产估价师。
“那比带着枪的人还恐怖。”她说。
海迪现在的工作是药物顾问,她挣的钱不够她照顾儿子,不够付他的大学学费,还有支付房租之外的任何事物。所以假如房东最后想办法把她赶出去,海迪说她就要搬去佛罗里达,她儿子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搬去跟她同住。目前她还在适应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的压力。
“真的很折磨人,实在太恐怖了,”她说,“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把暖气关掉,还是打算不做维修。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猜。现在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下两段楼梯就是1L公寓,也就是梅尔文·皮特(Melvin Pitre)住的地方。梅尔文40岁,已经在这里住了35年,他的母亲在这间公寓为他办过5岁的庆生会,如今公寓迫切需要修缮。他的兄弟姊妹长大之后搬出去了,但梅尔文留下来照顾母亲。
我遇见梅尔文时,他坐在客厅里一张很大的仿皮躺椅上,对着一台小小的平面屏幕电视。这间公寓很朴素,但有生活的痕迹。5月,当大楼被卖掉时,梅尔文的母亲正与乳腺癌搏斗,也开始有些心脏的问题。当新房东来向梅尔文自我介绍时,他的母亲住进了加护病房。某天新房东打给梅尔文,告诉他没办法继续住在这间公寓,因为公寓登记的是他母亲的名字,他们说他得搬去别的地方,或者可以帮他找到每个月1500美元的房子,这金额是梅尔文和他的母亲现在房租的三倍。梅尔文在工地上班,但工作并不稳定,他负担不起每个月1500美元的房租。
可能因为梅尔文付的租金是整栋大楼里最低的,新房东费尽心思要把他和他母亲赶出去,找借口说大楼基座要维修,梅尔文的居住环境有危险。他恳求他们至少等到他母亲出院,但后来他母亲戴着呼吸机回到家里,新的房东闯进他的公寓,对他大吼说别跟请得起大牌律师的人作对。
“如果没有我妈,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我想我会把他轰出去,”梅尔文告诉我,“我很挣扎,没这么做是因为我妈,她已经受了这么多折磨,最后还无家可归?那会让我崩溃。”他母亲在这件事后不久因为心脏衰竭去世。梅尔文最终选择上楼去跟吉内塔、海迪还有其他参与了里奇伍德理事会的邻居一起商量对策。
我最近面会过这栋大楼的所有租户,见面的地方在布鲁克林的住宅法庭,走廊上挤满许多其他类似遭遇的布鲁克林住民。一间法庭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清单,上面罗列着当周要开庭的其他近百余栋大楼名称。几乎每栋建筑物的屋主都是责任有限公司,很难去辨识或追溯真正的所有者。谢弗街租户的律师—里奇伍德布什维克长者理事会的罗伯特·康韦尔(Robert Cornwell)起诉大楼的屋主,迫使他们做修缮,目前看起来成效还不错。当跟房东商讨细节时,大楼的五个住户站在门廊,开玩笑说着他们在过去半年的抗争后变得有多熟。他们看起来很像家人,海迪从梅尔文的衬衫上拽掉线头,争辩着事件落幕之后该去哪里度假。
他们的律师带着好消息步出法庭:房东必须负责修缮。这场抗争似乎落幕了,但律师警告这群租户,房东可能会各个击破,意图对他们莫须有的欠租提告,迫使他们离开,用压力击垮他们。警告言犹在耳,但这天还是令人感到胜利的喜悦,至少目前他们是安全的,每户人家都在窗前摆上“禁止收购”的红色粗体字标语。
纽约市正面临住宅危机。也因为它开明的政治风气、它的财富、它优厚的福利制度,相较于美国的其他城市,纽约最有能力处理住宅危机。不像其他城市,选民们还在为怎么解决缙绅化问题僵持不下(除了几个票数很少又没有政党资金支持的“抗议型候选人”之外,旧金山市长李孟贤没受到什么反对。其他城市的市长根本绝口不提缙绅化的字眼)。纽约人似乎齐心协力,想找出进步的方案。2013年,纽约市民选出布拉西奥当市长,也说明了一切。布拉西奥本是个毫不起眼的候选人,他在民主党初选之前几个月的民意调查中都落在第四或第五,但他的竞选主张引起普遍共鸣―—他承诺要整顿前任市长布隆伯格造就的“双城记”。最后他当选了,领先温和派民主党的候选人两位数,并赢得大选几乎七成五的选票。
此刻的纽约比起美国其他城市,更有机会面对缙绅化的考验,虽说房租还是一样天天水涨船高,收入低的人还是被迫离开;不愿离开的人一天比一天面临更多压力,只为了要留下来。纽约比其他地方有更多武器,为什么还是不能阻止缙绅化的发生?
一部分的困难是,纽约的缙绅化历史超乎想象地深远,因此要挑战这件事,就如同要对抗这座城市百年来的政治。纽约是最早把缙绅化当经济手段的城市,要对抗它就像对抗洪荒。还不只这样,在纽约反对缙绅化,就等于起身对抗整套“成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理论,代表着激进的政治立场。纽约可能经济情况比大多数的美国城市好,但它还是仰赖房地产升值为主要收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0年代早期,纽约的商业精英越来越觉得穷人住得离曼哈顿的商业中心太近了,那里的土地很值钱,却被人群占据,充满破败住宅和工厂―—当时城市稽查员曾发现有42万名工厂员工住在五十九街以南的区域。纽约一些最有钱的人便聚集起来,共同商讨要怎么解决穷人住得离市中心太近的问题。1922年他们组织现在俗称的“区域规划协会”(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简称RPA),以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查尔斯·诺顿(Charles Norton)为首,成员有长岛市的地产大亨罗伯特(Robert De Forest)、罗伯特的叔叔弗雷德里克·德拉诺(Frederick Delano)等。他们认为提升市中心成高级住宅和商业区,并且投资外围地区的土地有利可图,因此外围的工厂要被迫迁出。
这群人规划了一套方案,完完全全预测到纽约今日的样貌:1929年的区域规划方案提到东河旁曼哈顿与布鲁克林侧的所有工业区,以及曼哈顿市中心全区,要从工业转型成商业或住宅。计划开宗明义建议将下东区的人移开,以“高档住宅”取代以往的平民家园,并要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华尔街的新大楼,因为下东区的新住民可能会在此工作。纽约最优秀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包括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重建纽约的时候也高度依赖这套计划。
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型开发计划暂缓,但纽约仍然致力于去工业化,用高价的房地产填满城市空间。去工业化几乎对美国每个城市都产生影响,但纽约是个特例:它刻意让本身的工业衰退。工业化1956年在美国其他城市达到巅峰,但纽约的工业―—多半是小型加工和成衣业―—在十年前就已经如日中天。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是美国唯一在去工业化时土地价值还会升高的城市。在其他城市还未跟上之前,纽约的规划者为新的城市形态铺路:集中发展房地产而非工业生产。1930和1940年代,纽约政府持续施压进行去工业化,同时政客们指出纽约的工业工作机会流失,是因为南方的便宜劳力以及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是个迷思:美国的工业化衰退时,事实上在几个大城市之中,除了得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之外,纽约的劳力是最便宜的。
1950年代晚期“区域规划协会”(RPA)支持的团体“当代土地分区市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for Modern Zoning)给纽约市施压,要求重新划分使用分区,纽约的去工业化状态进入白热化。大部分城市通过土地使用分区,隔开工业、商业和住宅使用(得州休斯敦是美国唯一没有做土地使用分区的大城市,但它的住宅区有其他禁制性的法律保护),但纽约把这套工具用得更彻底,可能远胜美国任何其他地方。虽然没有官方声明,但纽约主要就是通过使用分区来保持土地价值。假如工厂可以盖在第五大道旁边,那附近的公寓就可能变得便宜;如果整个纽约都被划作豪宅区,豪宅市场就会过度饱和,直至崩解。土地使用分区是为了让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保持稳定上升。纽约运用土地使用分区让有钱人享有特权,像西村或上东区就被划分为低密度住宅区,却又同时允许摩天大楼盖在长期贫困的区域。布拉西奥打算重新规划土地分区,以增加更多有市场价值又让人买得起的住宅,却很少提及西村或类似区域的状况,反而大范围地重新规划低收入的街区,如东哈林区(East Harlem)和东纽约(East New York)。土地重规划对穷人而言,一方面造成了不必要的打扰,一方面又让西村这些地方变得更珍稀昂贵。
1950年代,下曼哈顿充斥着大量的工厂,尤以苏荷区为最,这对城市精英来说似乎不太容易接受。“我不知道纽约还有哪里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不花大钱就能进行开发。”[12]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这么说道。市政府迫于“当代土地分区市民委员会”的压力,在1961年重新规划了几乎全市的土地,几乎是跟随“区域规划协会”(RPA)建议的方案,限制曼哈顿大部分市中心的制造业,尤其是水岸区。跟戴维·洛克菲勒开发东河(East River)周边,特别是曼哈顿广场(Chase Manhattan Plaza)周围街区成为商业区的计划正好合拍。戴维·洛克菲勒当时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如果没有土地的重新分区,也就不会出现城市里大规模的工业出走。1959年到1989年之间,纽约失去了60万个制造业工作。当时许多美国的城市都面临去工业化,但没有一个速度像纽约那么快。
祖金针对曼哈顿市中心的小型制造业者做研究,发现大部分业者如果经济状况许可,都想要留在原地。但土地重新规划意味着他们的楼房可能被转成公寓大楼,出租楼房比起工厂更有利可图,因而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关门大吉。根据祖金的说法,苏荷区是“投资氛围下的产物”,跟市区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分别,不是个有真实生活的街区。同时,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房地产(real estate)(取英文字头,号称“FIRE”)的就业机会增加了25%,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52%。效应就是有更多的FIRE业的人聚集在纽约,挤压了那些原本能在城市的工厂里挣得不错薪水的中产阶级的收入。
扼杀整个行业的就业机会,对经济会产生反效果,这道理或许并不出奇,但当纽约严肃看待1970年代以来持续恶化的就业率,政府官员似乎并不了解为何纽约的经济情况如此糟糕[18]。1947到1980年之间,纽约的制造业工作减半,中产阶级能做的工作不多,中产阶级小区陷入狼藉,整个城市几乎破产。
纽约接下来的做法会成为全美国城市的样板―—因为它是“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再发展策略的初始测试案例,卡特琳娜飓风之后所发生的,底特律现在所经历的,很大程度都可以追溯到纽约濒临破产之后的作为。
1975年10月17日,纽约市欠银行几近5亿,但市库却只有3400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请求福特总统(Gerald Ford)帮助这座城市脱困,福特拒绝了。隔天《每日新闻》(Daily News)刊出的头条成为美国史上最有名的新闻标题之一:“福特总统对纽约说:去死吧!”(福特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但他之前的一场演说显示他对纽约的财务烦恼毫不同情。)既然没有中央的及时援助,比姆便延揽了一位开发和公关人才理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来共商大计。拉维奇建议的方案,如今看来司空见惯,当时却可谓十分激进:他打算减少薪资,解雇员工,关掉医院、消防站和学校。他也说服教师工会掏出1.5亿的退休金帮助纽约脱困。短短几天内,由于刻意掏空工厂劳力造成的财务危机,拉维奇和贝姆让纽约变成高度依赖政府的城市,不只是经济上,辞令和理念上都是。纽约市在破产之前,已经是福利计划州的代表,比姆和拉维奇终结了这样的日子。
时至今日,这个城市摇摇欲坠濒临破产的那段时光,被视为领导人拯救城市的榜样。2014年拉维奇甚至被雇请去拯救底特律的破产。但纽约当时的转变更崎岖,到处都有大型抗议活动,工会聚集准备发起罢工,垃圾被丢到街上,抗议卫生预算削减。人们占领消防局,关注预算删减的情况,并请愿不要关闭大学校园。纽约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在垂死之前并非毫无反抗。
这般接近破产的状态不只是一种财务策略,也是实现一种新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手段。事实上,纽约在破产之后并没有削减太多预算,1980年代早期,政府支出再度年年增加,名目更加繁多,但不是用在帮助穷人的社会补助上,反而是帮助富人―—也就是补助开发。濒临破产让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以缙绅化作为治理手段的城市。
面临破产危机的几年之间,纽约的精英分子开始宣扬这座城市适合高档商务和观光。1979年一份由“20世纪基金会独立研究小组”(Twentieth Century Fund Task Force,另一个“区域规划协会”类型的组织,和官方关系密切)发表的报告,想象“后工业化”的纽约会成为全球资本的首都,“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纽约开启一系列观光宣传,包括“我 纽约”的字样到今天都还在使用。此外,纽约市在发全国观光财的同时,一边有系统地削弱对都市贫穷区域的服务。这就是当代“城市即生意”的滥觞。服务纽约的穷人被视为无利可图,更有经济效益的那群人―—观光客和有钱人―—变成这座城市最渴望的座上宾。
“我们不应该鼓励人们待在离工作机会一天比一天远的地方,”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的部长罗杰·斯塔尔(Roger Starr)表示,“别再让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移民住在都市里……该翻转整个城市的角色……城市不再是机会之所在……我们的都会体系仰赖一套理论,要把农夫变成工厂工人。现在既然没有工厂的工作机会,为何不让他继续当个农夫?”
他的发言引起众怒,斯塔尔下台了,但他的话语精准地代表了当时的都市政策。1970年代和1980年代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整个街区烧毁的画面还刻印在很多人的心中,电影和书也描写过房东为了保险金纵火,帮派在街区断垣残壁的空壳里横行。很少人知道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是恶作剧或绝望的住户干的,而是城市自己造成的: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纽约市就有意识地清除贫穷区域,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在给里根总统的信中提到这样的手段:“善意的忽略。”(benign neglect)。基本上是城市自己本身认为,移除贫穷区域的人比较好。
“火其实是一个小区病理状态的‘关键指标’,”莫伊尼汉写给里根总统的信上这么说,“它们先到,其他随后跟上。关于纵火的精神病学诠释相当复杂,它跟贫民窟会产生的几种人格特性有关……当种族课题受善意的忽略到达一定程度,纵火的时机就出现了。”
1976年,纽约市裁撤了34组消防队,因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认为裁撤这些消防站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兰德公司员工当时的信件往来显示,有些人知道这份研究报告并不正确。几乎所有关掉的消防队都位于布朗克斯(Bronx)以及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贫穷区域,后果直接且极为严重,大火摧毁了整个街区。在南布朗克斯的一些街区,八成的人口都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迁出,研究显示纽约衰退期间,大部分的火灾都发生在被裁减消防机关的区域。如果你研究纽约消防站遭裁撤地区的火灾频率图表,你会看到在消防站关掉之后,火灾的发生率就突然攀升,接着就会趋向平稳—这表示那些街区已经没剩下什么好烧的了。火灾现场的鉴定报告也显示了最受影响的区域:南布朗克斯、东哈林区、绿点区、布什维克和下东区―—以上所有区域今日都是缙绅化的目标对象。总的来说,1972年到1980年之间,根据流行病学家罗德里克·华莱士(Rodrick Wallace)的分析,有200万纽约人口被迫迁出正在历经缙绅化的街区,特别是城市水岸沿线。其中130万人迁至郊区,他们几乎全是白人,大概60万非裔和拉丁裔被迫迁到离市中心很远的街区。
这座城市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在1970年代晚期饱受祝融肆虐和刻意忽略,市政府又一心一意将自己定位成企业思维的机关,无视穷人的需求,为传染性的健康危机埋下伏笔。艾滋病毒(HIV)就出现在纽约市政府决定不再照顾贫弱人口的时候。
艾滋病的传播,并不是一个要清空最缙绅化区域的阴谋,反而是清空这些地方的后果:切尔西、哈林、西村、东村在1980年代时艾滋病最是猖狂。上万名男性死亡,大部分都是同志,黄金地段释出大量的空公寓。市政府也开始把扫荡目标转往多元性别族群(LGBT)聚集的区域―—也就是西边高速公路(West Side Highway)的码头和时代广场[34]。市议会在1985年通过一份健康条例,导致全市的同志戏院都关掉了。
纽约外围区域火灾频传,多元性别族群的安全空间都歇业了,疾病加速传播,纽约市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陷入危机,对有色人种、穷人、多元性别的纽约人来说尤甚。但这座城市开始有不同的度量经济的标准,而这套标准跟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幸福无关。1970年到1993年之间,美国已经流失了130万个制造业工作,其中纽约就流失了48万个。换句话说,美国失去了6.7%的制造业工作,而纽约则失去了63%的制造业工作纽约的工业衰退速度大概是整个美国的近乎10倍。但同时,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这三大行业开始承担起越来越高比例的城市税收,缙绅化推动者的媒体发言权越来越大,因此当纽约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遭遇另一波萧条,艾滋病肆虐,布朗克斯到处失火,但除了最受影响的地区,几乎没人在意。这波萧条很严重:失业率高达13.4%,三年内有40万工作岗位流失。但媒体却毫无动静,政治人物似乎也不为所动,因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纽约的经济体制已经变成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发展良好,似乎就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杀死一座城市》
作者:[美]彼得·莫斯科维茨
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
原作名:How to Kill a City: Gentrific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Fight for the Neighborhood
译者:吴比娜/赖彦如 | 出版年:2022-7
页数:284 | 定价:48.00元
装帧:平装 | 丛书:理想国纪实 ISBN:9787570325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