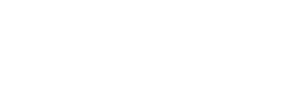制造消费者:1960年代西方启示录

【作者简介】安东尼·加卢佐(Anthony Galluzzo),法国让·莫奈大学讲师,在Coactis实验室主持“消费文化和市场新策略”项目的研究。
在所谓“漫长的60年代”(指从1958年到1974年)中,一种崇尚独特、彰显个性的反叛文化出现了。但这种“新精神”非但没有破坏商业秩序,反而通过宣扬富有个性的符号物,充当了消费主义的帮手。
1880年代出生的一代是第一批能够在身心上从社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在远离父母的地方享受了专属于青年人的休闲时光,并塑造了独立的“想象社群”,他们不再追随父辈们的文化,而是产生了自我意识,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代码。同时,他们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50年代的报纸为新一代人起了各种称呼:“青少年” “少年” “年轻人”(adolescents,teen-agers,décagénaires,jeunes)等,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青年文化,而且这些文化往往与一些图腾符号相关联,例如比尔海利与彗星合唱团(Bill Haley&His Comets)的音乐和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服饰风格等。20世纪中叶的年轻人之所以可以找到自我定位并团结一致,甚至在全世界范围里共享同一种文化,那首先是因为当时的青少年可以体验消费全球化,因为全世界都卖着一样的牛仔裤、点唱机、皮夹克和晶体管收音机。他们的自我意识建立依靠市场,并受到市场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叶,差不多整个文化和媒体行业都找到了一套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策略。
于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面向年轻观众的多媒体产品。在美国,所谓的“剥削电影”和青春片都得到了发展;新兴的青年杂志如德国的《喝彩》(Bravo,1956—)杂志和法国的《嗨!朋友》(Salut les copains,1962—2006)杂志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行了超过100万份。1960年代,青年文化规模变得极其庞大,以至于还出现了专门的电视节目,比如1961—1965年在法国播出的Age Tendre et Tete de Bois(稚嫩的年龄和木讷的脑袋)和1963—1966年在英国播出的Ready,Steady,Go!(准备,稳住,开始!),这一切都证明了青年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媒体和商业的文化。这套文化由音乐制作人、媒体老板、网络运营商共同掌控着、传播着。正是市场为年轻人提供了逃离家庭的机会,也是市场让他们可以进行远距离社交,形成他们的“消费兄弟会”。嬉皮士司图·阿尔伯特(Stew Albert)在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是真正的兄弟,因为我们是听同样的广播节目、看同样的电视节目长大的。我们有相同的理想……影响我想法的人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列宁或胡志明,而是《孤胆骑侠》动画片。”这句话完美地表达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部落效应”,由于电视等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前分散的青年们,现在团结在一个虚拟社群中。
1950年代,市场发明了“青春期”这个概念,当我们翻阅当时的商业资料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献都通过统计学详细说明了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和倾向。由于人口飞速增长,年轻人的数量逐渐增多,人们的积蓄也较之从前有了大幅提高,再加上年轻人比长辈更容易产生购买冲动,商家于是把年轻人设定为征服的“新目标”。婴儿潮一代的年轻人就在这样的市场里成长起来,广告商会通过专门针对年轻人设计的媒体向他们传播有针对性的信息,随时随地提供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产品。商家倾尽全力为青少年细分市场提供各种商品、信息、流行符号、价值观和规范。市场助长了青年的独立,也让孩子与父母的心理和文化差异越来越大。
市场和媒体的细分不仅导致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冲突,也让年轻人自己的社群内部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属于年轻人的大社群逐渐分裂为许多子群体,就像部落一样,这些分裂出来的每个小社群都有自己专属的代码和消费文化。1960年代初期的英国就有两个对立的群体,他们就是摩登派青年(mods)和摇滚派青年(rockers)。摩登派青年们喜欢绅士装扮,常常穿着紧身西装、三扣夹克、烟管裤和尖头鞋。他们继承和模仿着各种高雅的风格,如维多利亚时代贵族风格、法国新浪潮风格和意大利奢华(Dolce Vita)风格。他们喝卡布奇诺,听现代爵士乐和节奏布鲁斯,骑着韦士柏(Vespa)或兰美达(Lambretta)踏板车。而摇滚派青年则穿着牛仔裤、皮衣,佩戴各种金属饰品,喜欢听摇滚,喜欢聚集在一起,展现他们强大的男子气概,他们骑着硬朗的摩托车,就像飞车党。
年轻人的文化就是商业的文化,他们的群体身份通过服饰美学和标志物来表达。青年们的不同小社群都有各自认同的消费代码,而这些代码形成了一种传达态度和信仰的语言。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同与不同”的基本机制,只有通过对符号物的拥有和展示、通过购买特定的象征性服饰,青少年才能加入一个群体,也和其他群体划清了界限。这种“部落认同”有时还会导致冲突。1964年摩登派青年和摇滚派青年之间在英国多个城市的海滩上的大打出手,吸引了英国媒体的争相报道。然而,年轻人之间的暴力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青年帮派之间的血腥冲突自古以来就有了,然而,以前年轻人打架多是为了抢地盘、争土地,或者是为了向邻村人展示本村的力量,现在则大不一样。随着20世纪中叶年轻市场文化的出现,地域竞争被消费者行为引发的“部落”竞争所取代,现在的年轻人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推崇的市场偶像不一样,或者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标志物不一样。
1950年代的世界各地常有青年团伙暴力行为发生,如法国的“blousons noirs”(黑夹克)、意大利的“teppisti”(小流氓)、荷兰的“nozems”(刀)、德国的“halbstarke”(恶霸)、丹麦的“naderrumper”(裸臀),这些青年破坏者们手里挥舞着自行车链条和破瓶子,在街头打架和争斗,令人惴惴不安。尽管这些暴力群体极为少数,但他们却引起了整个社会对青年人的质疑。当时的报纸上有很多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对“青年叛乱”发表评论。他们认为这种帮派暴力似乎没有动机、非理性,所以就显得更加严重和难以置信。人们把他们称为“无缘无故的叛逆者”,这些年轻人既不为党派也不为宗教而争,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躁动、如此具有破坏性、如此愤怒?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身上会有这种情绪?
于是,分析家们试图通过这一代人的偶像找到问题的答案。《飞车党》里的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无因的反叛》中的詹姆斯·迪恩都是青少年追捧的典型。这些电影角色都是反抗成人世界、拒绝墨守成规的形象,很有独特性。他们四处流浪、找寻自我。这种生活态度在一些年轻人中引起共鸣,这些角色也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于是他们模仿这种冷漠、挑衅的态度,似乎这样就可以无形间离这种形象更近一些。科普弗曼(Copfermann)分析说:“不同于以前流行的‘异域’超人形象如人猿泰山、佐罗等,新的流行故事更乐于塑造平日生活里的英雄。当他们在类似现实的场景中出现时,对人们的影响力就更加显著,也显得更易接近了。”当时所有年轻人的亚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拒绝传统而严肃认真的文化,他们用叛逆的态度反抗着上一辈的墨守成规,他们提倡随性、坦率、超脱……简而言之就是“酷”。任何形式的不服从和挑衅都会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小到剪个古怪的发型、大到恶劣的违法行为,都有人敢去尝试。那时,新流行的摇滚舞也为这种解放的渴望提供了一个物理出口。詹姆斯·迪恩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主要偶像,正是因为他体现了像他的电影标题里所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他终生追求着浪漫的叛逆和虚无主义,直到24岁因车祸而逝世。
在新兴的大众社会中,自主性和个人自由更加难以维护,这也许是年轻人有如此大情绪的原因。1950年代,生存焦虑无处不在,人们的生活在工业的影响下变得标准化。在大型公司的控制下,工作与消费各占据了人们生活的一半。现代社会是组织性极强的社会,破坏了不少个性。自1920年代以来,广告又为人们增添了更多的焦虑。微笑和整洁的家庭、奇妙的家用电器、完美的住宅、修剪整齐的草坪、锃亮的汽车,这些场景成了美好生活的模板,但也是一成不变且毫无个性的噩梦,人们的自主性被掩埋在了从众行为之下。
于是,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意义危机”,并开始拒绝墨守成规。这种心态弥漫在整个1950年代的美国。那个时期,很多小说都描绘了主人公是怎样陷入日常舒适圈里的,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就是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畅销书《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该书于1955年出版,随后于次年改编为话剧。在这部小说中,一位二战老兵一直保留着他旧时的经验习惯,穿着过时的装束,做着一份小行政人员的工作,努力过着他单调的生活。当时的另一本畅销书,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则解释了富足生活是怎样影响普通人的心理的。根据书中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做出决策更多的是“外因决定”而非“内因决定”。理斯曼用学术语言表述了对从众的极大恐惧。当时其他畅销书作家也都有类似观点的作品,如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White Collar,1951),威廉姆·怀特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Galbraith)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其中一本书格外畅销,把当时人们的焦虑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就是于1957年出版的万斯·帕卡德的《秘密说服》。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提到过这本书了,最初就是这本书谴责广告有操纵他人的能力,声称广告可以向消费者销售他们不需要的产品。帕卡德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了“潜意识广告”的存在,也就是在一些非广告的作品(如电影)中悄悄插入广告信息,从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引发公众的消费欲望。《秘密说服》的作者把广告描写为一门可耻的技术,但是如我们第七章里提到过的,广告的效力实际并没有那么大。但无论如何,帕卡德的论调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的,在当时的氛围中,人们都相信广告拥有洗脑和催眠的力量。
于是,在这种焦虑情绪蔓延的漫长的60年代,一种批判从众的新思想流行起来了。这种理念从存在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并很快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这些理论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Adorno)、信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赖希(Reich)和马尔库塞(Marcuse)以及情境主义者德波(Debord)、瓦内格姆(Vaneigem)和列斐伏尔(Lefebvre)。他们将各自的理论因地制宜地运用着,但这些想法最终都汇流到了一处:异化。这套时髦的论点5被当时的很多评论家所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操纵了人们的享乐心理、制约了人们,让人们变得被动和从众了。
该领域的一部著名作品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于1955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批判发展了弗洛伊德“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的观点。马尔库塞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最初对欲望的压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是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劳动掌握程度的提高,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这种压抑就变得非理性了。人们现在能从异化劳动和牺牲中解放出来,但社会对人类的束缚仍然很牢固,现在它通过种种社会制度维持。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谴责的“过度镇压”的非理性和无用,他认为这会最终导致废除它的反抗。
从这个新视角来看,这场斗争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自觉进行的,而不是在经济政治层面发生的。这些新左派思想家所述的革命理想不再是推翻国家机器、夺取统治权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意义不再是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要求解除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从而实现人的真正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新左派的个人主义理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个人主义的左派人士希望的“新新人类”(nouvel homme nouveau)是一种能从集体和集体所暗示的必要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存在。他们的矛头不再指向有产阶级本身,而是指向一种压抑人性的资产阶级心态―—它体现为将压抑内在化的清教主义。为了实现内心的解放,他们提倡与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压迫制度作斗争。与资本作斗争,就是与异化作斗争,就是与最原始的人类本真重新建立联系。这种新兴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治疗和自我为中心,希望通过愉悦、想象、享受活动来改变自己,而这些活动实际上也是压抑制度的一部分。
本性的解放、欢愉和享乐主义在罗斯扎克(Roszak)眼中都是“被压迫者的精神解放”。正如欧内斯特·阿尔芒(Ernest Armand)所说,新左派的观点实际上和本世纪初的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在“找寻、挑衅、品味、欣赏撩人的情绪、激动人心的感觉、强烈的愉悦、令人眩晕的冒险,它们都是生活给自信者和喜欢热情、生动、自由愉悦的人的馈赠……”这是从共产主义革命到阶级内部革命、从工人阶级到自我阶级的转变。这一切尤其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得到体现,人们高呼:“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那些自发的激进革命者宣称:“在把资产阶级赶上街头之前,要先把它赶出脑袋。这就是革命的过程!”
1960年代出现这种具有激进和主观性的思想被称为“反主流文化”(contre-culture)。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为了“换一种生活”,而采取与资产阶级标准相反的生活方式。因此,革命成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最终也成为一种消费方式。反主流文化也有其深刻的商业意义,而且是以一种非常疯狂的方式来展现的。人们将物品作为一种语言,而购买一件商品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和反叛。为了让外部的人们了解革命,革命者有必要通过大肆展示反主流文化和自己的新潮态度,来表示对资产阶级和传统社会的拒绝。
在这种反叛模式中,年轻人和对社会不满的人们崇拜着一些边缘化的英雄形象。那些蔑视社会标准的人显得更真实,他们不和资产阶级标准同流合污,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标准。在美国,不法之徒、犯罪者以及马龙·白兰度这样的银幕偶像激励着摇滚小青年,就像法国暴乱者们崇拜博诺(Bonnot)黑帮一样,正如嬉皮士杰里·鲁宾(Jerry Rubin)写的那样:“《雌雄大盗》里的邦妮·派克(Bonnie Parker)和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这些传奇形象都热烈地追求着真实和纯粹。当社会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的规范,对旧有社会习俗的侮辱行为就被看作是一种激进的政治行为,而罪犯则成了所谓的抵抗战士。反主流文化尽管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所鄙视,但这些追随者其实就像流氓无产者一样既浪漫又冲动。从那时起,不少西方青年喜欢穿着像抢劫犯一样的“黑夹克”,这种看着像“暴徒”的打扮,吓坏了老一辈人。穿着优雅的摩登派青年其实也在模仿伦敦街头的夜店装束,而嬉皮士则像乞丐一样穿着破布。在这些截然不同的风格中,年轻文化汲取了专属于他们的代码,他们追求独一无二,追求风格。
边缘化的形象和反叛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想象、新的风格,人们产生了加入其中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显得独特。这和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的资产阶级为了让自己显得出众和独特而做出的“慕洋”行为有类似之处。对于19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加入少数派、参加激进的活动、让自己显得高深莫测,都能为自己的身份带来象征性的优势。反主流文化的推崇者“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边缘化的”、“在别处的”、“平行的”、地下的、“体制外的”。
同时代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们也一样表现了对“独一无二”的追求。我们此前已经在19世纪原始消费者形象的章节里介绍过他们了。波西米亚艺术家极具独创性和创造自我的能力,他们不满资产阶级惯有的那种谨小慎微,而是致力于美和充满激情的创想中。他们追求的那种艺术,与所谓的优良传统相距甚远,波西米亚艺术家的形象既像是一个饱受折磨的酒神、一个被禁锢的怪人,又像是一个被家人抛弃的极端主义者,与社会毫不相融。他们为了追求艺术,不惜冒险和违法,并沉溺于酒精、毒品和疯狂之中。他们既像是循规蹈矩的破坏者,也像是新社会的助产士,康斯坦特·纽文惠斯(Constant Nieuwenhuys)曾这样评论道:“从事创造的艺术家必须要扮演革命者的角色,要摧毁空洞而烦琐的旧时代美学,以唤醒我们每个人被忽视的创造本能和潜力。”
艺术家是终极的反叛者、越轨者,随着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波西米亚艺术家们所做的工作如绘画、写作等,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姿态。在他们的世界里,艺术家通过一系列行为和态度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从而表现一种独特之美。因此人们要学的,是像艺术家一样穿着和生活,而不是真的去成为一名艺术家。对艺术家的模仿成了一种反资产阶级和反规范的理念、一种追求离经叛道的流行趋势。像这样,1960年代的年轻人们热烈地拥抱“艺术家风格”,追求着“独特就是好”的理念,就像19世纪的丹迪主义者一样。这一系列追求独特的行为最终都成了消费动力的基础。人们要想拒绝做普通人,就要通过拥有某些东西来证明自己远离了庸俗。虽然这一切都属于反主流文化,也是反资产阶级美学的表现,但这些行为仍然遵守了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出众而消费。因此它们背后的机制是一样的,只是判断标准变了。
边缘人、小混混、艺术家听起来都是一些“酷酷的”角色,其实他们都可以被视为丹迪主义者矩阵形象的变体。和丹迪主义者一样,他们都追求一些特定的彰显身份的符号物,并抱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从而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因此,反主流文化的本质也是一种消费文化,因为它基于人们的自恋和展示欲望,基于人们想向外界展示出自己所拥有某些符号和特点。所以,反主流文化也一样要遵循既定规矩,需要通过特定的符号物,来展现玩世不恭和不循规蹈矩,通过让自己与众不同来获得一些社会收益,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份。所谓的“酷”,意思就是随时随地都保持一种假装冷漠的姿态。这种“酷”文化彰显着一种傲慢和讽刺的情绪,有着丹迪主义的风格,是一种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激烈、超脱又叛逆。
反主流文化构成了一种对立的美学,在这种美学中,个人不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角色来定义自己,而是将自己定义为渴望和象征的主体。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浪漫和艺术的追求中,是因为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商业规模的扩大。正是因为西方经济在漫长的6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青年才可以“逃离平庸”,去追寻和体验浪迹天涯的生活,而不必担心基本的衣食住行。那些追求流浪的年轻人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他们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才有钱投身于嬉皮士运动、寻找乌托邦。当那些追求小众的人们不远万里到尼泊尔去旅行时,也是凭借着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大,才可以在当地每天只靠1美元生活。而与此同时,嬉皮士运动的领导者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鲁宾则在华尔街举行的一场节日活动期间不计后果地烧掉美元,呼吁消灭金钱。同样在那个时代,在美国最富裕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州,反主流文化集体“掘土派”(Diggers)也出现了。他们倡导的“free”既是“自由”的意思,也是“免费”的意思。在旧金山,他们开设了“免费商店”(free stores),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留下商品或拿走商品。对此,爱丽丝·盖拉德(Alice Gaillard)评论道:“那都是因为美国太过富有了,人们随地都能捡到富裕阶层丢下不要的东西。……1966年的美国‘掘土派’掘的并不是真正的土地,而是城市人挥霍和浪费的剩余物。”
反主流文化的追随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寻求原始和本真的自我。为此他们用上了不少时下的“自我技术”,例如“新纪元医疗理论”就结合了心理学、精神分析、东方神秘主义和西方宗教的各种理论。这一系列理论被称为“神秘深奥的星云”,对其做出贡献的有1962年成立的伊莎兰学院(Esalen Institut)的人文心理学科,以及1971年创建的艾哈德研讨训练班(Erhard Seminars Training,EST)。这些心理疗法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和寻找自我,目的是让参与者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帮助他们找到被压抑的原始自我。当他们找到自我后就得到了解放,也就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个性,从而可以更好地表达自我、更好地去爱、更好地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类似的心理辅导课程通常以会议和谈话小组的形式开展,参与者会在“治疗师”的指导下通过心理剧、歌曲、按摩和冥想进行互动。
在漫长的60年代发展起来的多种反主流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存在主义的特征,追求本能和愉悦,甚至追求无政府主义,反对官僚、冷漠和压抑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反主流文化的追随者都试图实践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的理论,即要反对资产阶级就要去攻击资产阶级的基础心态:严谨、朴素节俭和因循传统。从更政治化的角度来看,一些人认为对上层建筑的攻击可以蔓延到对经济基础的打击,一旦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精神,就可以推倒整座大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仅仅是一种资本自我产生的模式,它的价值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积累的逻辑可以容纳所有不从根本上反对它的意识形态。
所以,反主流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对资本主义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解放自己的欲望也就等同于让消费欲望自由发展、需求也就无限增长。正如我们所见,人们对自我的追求、对表现的渴望和对规范的反抗助长了“同与不同”机制,使得人们越发倾向于通过物质来实现自我表达、自我展示。因此,反主流文化的“情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化剂,它打破了保守主义的秩序、刺激了商业。同时,这些借助符号物展开的斗争和人们对自我的追求却并没有对政治产生真正的影响,人们不断强调这些意识的解放,但是却对革命最基本的价值问题、制度问题、生产和利润的分配问题避而不谈,显得不痛不痒。
60年代的年轻人抛弃了老一辈的储蓄习惯,也抛弃了节俭、远见和禁欲的精神,他们的新心态变得更适应现代社会。这是工业发展刺入并打破人类社会的体现,物品在全球被复制、被广为传播,加速着人、商品和他们的形象的流动。这一代人之所以成为旧式严谨保守心态的反对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成熟理性,而是因为1960年代的年轻人就是在物质的时代长大的,这一切都使他们的意识形态转变,并感受到所谓的压迫感。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60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上层建筑是与其经济基础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种精神上层建筑具有双重性,既包括生产和工业关系所依赖的严谨和理性的一面,又包括通过消费支持自我表达的浪漫和冲动的一面。这“两种对立但互补的论调构成了一套现代观,一面是功利主义,另一面是浪漫主义”。
这种双面性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融合着。反主流文化者的理想首先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不可分割的、真实的存在,一个享受生活、创造自我的主体,一个现代的、有成就的、不可简化的主体,作为统计数据在社会规律之外发展。但这种对原始或本真的幻想本身就是一种“鲁滨孙式文学”(robinson nade):不切实际的自我欺骗,仿佛人可以摆脱社会主导、摆脱一切外界约束。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内涵就是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追求,反主流运动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古老的美国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庆贺着美国先驱、枪手和他们的西进运动。在反主流文化价值观中,人们对国家和政党不信任,更加自我,更想要“选择”的自由。这些价值观在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时代被理解和接受。
反主流文化的支持者经常谴责那些把反主流文化变得商业化的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商业社会试图“招安”这些新兴文化的手段。在他们看来,机会主义的商家们为了一己之利,榨干了反主流文化的创造潜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商业创造出来的“山寨的”商业反主流文化,是不同于真正的、原创的反主流文化的。市场体系就像邪恶的普罗透斯,把反对论点统统同化,并从中获利。不过,这种“招安”论里提到的“原始而纯粹的反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与商业分开的。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解释的那样,反主流文化从本质上就是商业的,它只能在基础设施完善、通信发达、市场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摇滚乐队只能通过录音广播技术才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只有经济基础完善了,猫王(Elvis Presley)才能登上电视、影响无数反主流文化爱好者。
新兴的青年文化也是媒体全球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媒体的大量曝光,那些亦是艺术亦是犯罪的各种过激行径也就无法传播开来。那时候很多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都试图通过积极报道这些青少年的出格行为来吸引眼球,甚至把一些小众文化故意夸大:“垮掉的一代”、黑夹克、因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电影而引发大规模模仿的嬉皮运动等。因此,媒体可以说是“另类”文化的第一推手,而市场则向年轻人贩售这些文化。
年轻人往往在咖啡馆、爵士酒吧、夜总会等地聚集,而这些社交场所都是商业化的。年轻人青睐的流行风格则都是由先锋服装精品店引领的,这些受到欢迎的时装也因此占据了市场的一席之地。另外,1960年代后期流行的盛大音乐节上也处处是商业,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上不仅有演出,还有数不清的商店和小商贩。正如第五章所述,正是从这一代年轻人开始,休闲活动发展为一个专门的行业。以前的人们在家附近的小社群里和各个年龄段的街坊邻居们一起休闲,而后来的年轻人则更喜欢在专门为娱乐而设计的商业空间里游乐。这些新的商业设施为年轻人们提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让他们从社群中独立出来,自由生长。因此,当反主流文化的小青年们谴责商业对文化的“招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商业其实从始至终伴随着他们文化的成长。商业让年轻人群体从小众的、不起眼的地下市场变为清晰的主流市场,这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过程、是正常的市场增长趋势。真正的问题是,随着反主流文化的广为传播,这种文化失去了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当一种标志物变得“流行”时,它的象征性价值就减少了,也就是说,它不能让其拥有者感受到出类拔萃了。因此,从这种角度看,那些反对小众文化商业化的人其实和第三章的资产阶级收藏家持有一样的心理,当他们看到那些他们所瞧不起的、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也掌握了他们的兴趣爱好时,他们就会感到恼火,并立刻要去找一些新的方式让自己重新变得出众起来。
1960年代的特别之处是人们不再将领土或阶级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习惯成了重中之重。“社群”不再局限于人们的原生地,也和人们从事的生产无关,人们住进了各种虚拟的、全球化的社群,而入场券就是用于包装自我的符号。这些消费者部落让年轻人可以自愿选择自己归属的群体,而越是那些距离日常生活遥远的群体,就显得越有价值。人们既可以加入穿衣打扮都有着上层阶级色彩的摩登派青年阵营,也可以加入嬉皮士,像不修边幅的底层人群一样随意放荡。这就是19世纪末新市场社会的形象,人们的地位全都取决于外表。“当我戴着一顶我喜欢的帽子出门时,这不仅表达了我的心情,也展示着我的风格。人们就这样彼此欣赏着各自的风格,并互相回应。……这些行为从整体上来讲不是联合一致的,而是有来有往的。当我们做某些行为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有其他人在场见证,这样我们做这件事才有意义。……城市里的人们就是这样开展着交流。”
市场已经逐渐具备了给予消费者某种身份的功能,多种多样的商品美学对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这是市场细分的时代,市场被划分为不同的买家群体,商家据此提供差异化的产品。通过向特定消费者群体传播特定信息、图像和产品,商家逐渐建立起了一种针对特定人群的消费文化,从而加深这类消费者群体的思维定势。这种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和定位也不断改变着人们。
细分市场使得一家公司可以利用市场中的所有机会,为每个群体提供相应的品牌、风格和产品(第一章里我们就提到过多芬和凌仕这两个联合利华子品牌的矛盾性)。细分还可以使消费行为不断建立和推延。因为人们不再追求统一的风格和形式,而是根据时下流行的多样化风格,以及消费者想展现出的身份来完成消费行为,于是,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新风格很快就过时了,商品的流通更加迅速。当每个新的小群体建立时,他们都希望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例如,朋克运动就是嬉皮士风格和价值观的完全颠覆。不管再怎么惊人的新玩意儿,一旦在市场上推出,大家很快就习以为常、不以为奇了。当旧的时髦商品变得“烂大街”,人们就需要再一次寻求让自己出众的消费方式。在反主流文化体制下,人们追求的符号物从贬值到更新的流程越来越快,时尚周期也比以前更短了,这一切都进一步刺激了生产。所以说,人们反墨守成规的心态(anticonformise de masse)其实比标准化和统一的社会更适合资本积累。
广告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广告活动是反主流文化者所厌恶的。那个时候,商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声音向大众展示新产品,申明应遵循的规则和标准,告诉他们只有买了某件商品才能融入社会。这是一种专制的、家长式的广告,他们不断推出“最高级”的东西来教导被动和懒惰的大众应该怎么做。这种在20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广告形式在1960年代崩溃了,从此,广告修辞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能体现这场“文化革命”的广告就是1959年由恒美广告公司(Doyle Dane Bernbach’s, DDB)为德国汽车品牌大众(Volkswagen)制作的广告。这些广告没有遵循以前主流市场广告的基本原理,也和汽车行业的既定准则相悖。直到1950年代末,汽车广告主要是一种权力想象:它们赞扬机器的技术卓越、动力高效和给驾驶者带来的威严,通过各种图片展示车身的闪亮外观、舒适的内饰和发动机的能量。在这种广告带来的想象中,汽车是卓越的符号、成功的象征。然而,大众汽车采取了相反的表达方式,推出了极简的黑白广告,广告中的汽车以小巧而低调的方式出现。在大众汽车最著名的广告“小处着手”(Think small,1958)中,展示了著名的甲壳虫汽车,广告里的车子很小,孤零零地待在空白页面的中间。大众汽车甚至还做了广告,自嘲简陋:“量入为出,量力而行”,自嘲狭小:“它让你的房子看起来更大”,自嘲难看:“丑陋,缓慢,吵闹,昂贵”。而这种自嘲式的谦虚是相当叛逆的,因为它其实讽刺的是整个汽车工业和美国大品牌(凯迪拉克、雪佛兰、庞蒂克等)的“计划废止制”。当其他品牌每年都提供新型号的汽车、配上越来越奢侈的各种颜色和装置时,大众汽车却反其道而行之。
1960年代,大众汽车的叛逆之举导致许多汽车制造商也重新调整了策略,纷纷模仿DDB开创的反主流文化和反主流宣传的风格。沃尔沃在1964年曾愤世嫉俗地宣称自己的车是“不爱车之人的汽车”,并以此嘲讽那些每年更换汽车的人。1965年之后,美国制造商们也改革了他们的广告文案,开始宣扬一种幽默的、不墨守成规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比如道奇(Dodge)汽车就因为“你准备好加入道奇叛乱了吗?”的广告语被誉为独立和叛逆的象征。因此,人们对循规蹈矩的反感和反主流文化的兴起并没有给广告业带来多大的困难,只需要调整广告的语言风格,就可以很好地适应新的文化。如果墨守成规令人厌恶,那么广告就可以变得不墨守成规。如果公众不喜欢汽车广告强调身份地位,商家就可以通过广告反对身份地位论。这是广告从刻板到时髦的转变,广告的内容也不再遵循古板的老一套,变得更加轻松顽皮,更加符合时尚流行的节奏。这类广告提出了一个悖论,它号称某种新的消费方式是为了让人们不要被旧有的消费所捆绑,这个看起来荒唐的论点完美地消解了人们对消费的批评,这就是“麦迪逊大道对万斯·帕卡德的回应”。广告口号仍然存在,但它们现在强调的是自由,而不再是卓越,他们的言辞从“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这类说法,改为了鼓励消费者“做真实的自己”。
在这样的转变发生后,广告商也随之改变了角色和姿态,他们不再是向大众传授市场价值的权威,而是赞美本真的幽默大师。通过各种自嘲、反讽、超然和无礼的广告言论,广告商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并以一种相对友好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因此广告变得反主流、变得酷了起来,它们不再展现规范、制度、大众社会,而是成为上述这些东西的反对者。1960年代初期的广告商以反主流文化风格重塑身份和广告语的行为,其实就是商业广告商的核心,即掌握时代潮流、抓住最流行的符号、构建和产品相关的联想。
然而,广告商是刻意借用反主流文化的修辞吗?历史学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认为,这种广告语的转变,即这场“文化革命”,其实在1965年就完成了,也就是说,早在反主流文化思想在媒体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为所有人所知之前,广告商就已经开始转变了。“1960年代后期的反主流文化广告,很容易被人解释为是对反主流文化的‘回收’,但是实际上那些广告的方式与最初大众汽车广告里时髦的消费主义是一致的。”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广告和整个商业世界都是促进反主流文化思想诞生和传播的因素。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是广告商在旧有广告越来越低效时,盗用了反主流文化的代码用于广告。
很多人认为反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广告辞藻中被滥用,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因为广告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美国1968年的著名抗议者杰里·鲁宾发表的宣言似乎就借鉴了不少广告语的造句方式,他说:“革命是新人类的创造。革命意味着新的生活。在地球上,在今天,生活就是生活,革命就是革命。”那时很多新左派群体(如嬉皮士和掘土派)都喜欢用简短有力的句子当作口号,这些句子只是单纯地连在一起,没有任何论证结构。这是一种由挑衅和断言组成的语言系统,茱莉·史蒂芬斯(Julie Stephens )认为,它更像是“广告语和牛仔电影的混搭,而不是左派的宣言”。美国新左派的这种措辞与几十年来主要品牌的广告口号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语义联系。杰里·鲁宾的“去做吧!”(Doit!)就可能来自耐克(Nike)的“Just Do It”。自1960年代以来,很多广告语都以自发的表达和不妥协的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理,例子数不胜数:苹果(Apple)的“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雪碧(Sprite)的“为做真实的自己许诺”、锐步(Reebok)的“我就是我”、麦当劳的“来吧!就是你!”(Venez comme vou sêtes)等。现在典型的广告语都是在宣扬人们“成为自己”,并将商品尊为解放自我的工具。
于是,反墨守成规成为商业传播新的根本轴心,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苹果的品牌资产十几年来都在一众跨国公司中名列前茅。自公司成立以来,苹果公司就一直喜欢“讲故事”,而这些故事都致力于建立和维护该公司的叛逆形象。在Macintosh(麦金塔,常用简称Mac)发布的1984年,苹果委托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以《1984:麦金塔》为题制作了一则电视广告,展现了一个工业化和反乌托邦的宇宙。在礼堂中,巨大的屏幕上是一个有着乔治·奥威尔小说风格的“老大哥”,他对着昏昏欲睡的人群发表傲慢的演讲,这时,礼堂里一名年轻的女运动员跑了过来,她身着红色短裤和白色麦金塔上衣,身后是士兵在追赶,但她还是用尽全力用大锤摧毁了巨大的屏幕。然后画外音评论道:“1984年1月24日,苹果将发布麦金塔,你会明白为什么1984年不会像小说《1984》里那样。”在这个想象中,代表极权主义力量的“老大哥”指的就是IBM,它的形象是冷酷的、工业化的、没有灵魂的。而苹果则是那个解放者,它把计算机的控制权从大企业和政府的魔掌中夺走,供给大众使用。苹果公司从始至今一直热衷于这种“讲故事”式的广告宣传,目的是告诉大众,苹果公司不是一家私人营利机构,而是旨在“帮助人们凌驾于最强大的机构之上”。简而言之,苹果几十年来的所有言论都恪守着反主流文化的信条,与其他墨守成规的电脑用户不同,苹果用户仿佛拥有艺术家、反叛者的身份,他们通过购买苹果电脑,彰显自己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个性,因为他们就像苹果的口号一样,有“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这些有反叛意识的品牌,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规范,大企业们也不能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以家长的口吻来说教了。它们摇身一变,装扮成摇滚歌手、说唱歌手或具备时下流行元素的各种形象,以这种方式来迎合时代思潮的变迁。由于1960年代的种种转变,以前那些被认为不正常的边缘群体成了品牌们争相联合的对象,并给品牌带来了无价的象征资本。![]()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制造消费者》
作者:[法]安东尼·加卢佐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 出品方:万有引力
副标题:消费主义全球史
原作名:LA FABRIQUE DU CONSOMMATEUR:Une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marchande
译者:马雅 | 出版年:202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