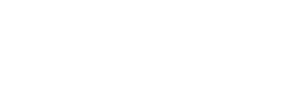另类流浪:精神内耗的解药还是坑?

数字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到快乐的地方去工作,你的技能比护照更重要。”
人才招聘网站Jobbatical不仅slogan听起来悦耳动听,更关键的是,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深得IT自由职业者的欢心。
这些机会都是全球性的,遍布美国、欧洲、亚洲,大都是为期三到六个月的短期项目,恰好也是环球旅行者在一个陌生城市新奇感的上限。
比如马耳他一家客户营销网站在招聘首席网络工程师时,强调可以“住在地中海温暖的岛屿,一年四季都有好的天气”;Uber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计划招聘一个项目软件经理,称这里的综合生活成本比旧金山低16%,不过这听上去好像并没有低太多,但是对于月光族来说,足够给晚餐加个鸡腿了。
这家网站的拥趸们正是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如果你按照英文的字面,很容易把这波人误解为数字时代流浪汉,生活的弃儿,或者沉迷在网络世界里的御宅族,被迫离开母国走四方的“迷失的一代“。
恰恰相反,这是一波拥有强大选择能力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年轻而多金,身怀一技之长,主动地选择了做一个地球村的流浪汉,他们热爱远程工作,赚着第一世界的美元到东南亚的碧海蓝天中去低调挥霍。
维基百科对数字游民的定义中,也突出强调了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务缓冲能力”。不过,在美国,他们也只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小撮。在热门的问答社区Quora, digital nomad 内容标签之下,关注者只有数百人。
相比英文名里的边缘姿态,在简体中文世界里,digital nomad的译名―—数字游民―—显得如此优美,包含了中国年轻人对不同于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以至于才会产生类似这样的大讨论:是不是只有码农才能做数字游民?
他们不是数字游民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数字游民在中国存在的两个大误会。
误会之一,数字游民就是自由职业者。
领英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自由职业者报告》发现了中国自由职业者有这么几个特点:
· 年龄上,主要为工作年限不长的年轻群体;
· 职业上,上目前可分为三大类:专业人士、销售代理/无底薪推销员、个体户。其中专业人士主要指包括摄影师、设计师、独立翻译在内的拥有专业技能的自由职业者;
· 在地域上,他们更广泛地分布于中小城市;
· 在能力上,他们相较固定职业者,拥有人脉更广,更多的技能,他们拥有的核心技能大致可分为语言类、设计类、文案营销类。
· 显然,数字游民属自由职业者的一部分,最大的区别是,数字游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得。随着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未来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将更多地通过互联网来获得。
误会之二,soho族就是数字游民。
最早是开发商在中国炒热了soho 的概念。在上下班动辄需要数小时的北上广深,主张在家办公的soho,一度火热了一阵子,并且带动一批loft项目的销售。但第一批先锋很快发现soho生活的弊端。
网友暗夜教主2007年就在豆瓣上吐槽:“自从soho以来,我渐渐发现上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赚得工资,而是还有一个同事的交往空间。自从一个人soho以来,生活开始孤单乏味,这时候才发现,即使是一个无聊的工作,钱也并不是它唯一的产品。”
与在家办公的soho族不同,数字游民尤其忍受不了蜗居一室,他们志在四方,当然也有效避免了soho 族社交圈子过窄的问题。地产界也与时俱进推出了联合办公空间的产品,作为soho 的迭代补充。
如何成为数字游民?
不过,与自由职业者和soho一族类似的是,成为数字游民,还需要跨过关键的三道门槛。
第一道门槛:足够长的一技之长。
除了程序员外,律师、会计、编剧、音乐制作人、心理咨询师、自由撰稿人、教育辅导都非常适合做数字游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突出的专业能力。
遗憾的是,这些卓越的专业能力,通常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
就像一万小时定律所说,几乎没有捷径可走。人类脑部确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理解和吸收一种知识或者技能,然后才能达到大师级水平。顶尖的运动员、音乐家、棋手,需要花一万小时(其实是虚指),才能让一项技艺至臻完美。
来自美国的博客作者R.L. Adams就认为,有志于从事社交网络营销的同学,就相当适合做数字游民,并且他还给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建议:包括发布一部以社交网络营销主题的电子书,然后开设一个博客,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创建一个在线课程直接向用户收费。
这路数,听起来和国内的“知识付费”很像,但最关键的一点是xx也没法帮助你的―—如何建立专业能力,他说的主要是如何展示这些能力。不过,敢于展示自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基层政府工作了七年多后,西皮士在2017年初决心离职,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不久,在豆瓣上发布赞助离职计划,通过每人500元的网络众筹,制作和销售他的音乐专辑。2017年,2017年共有249位听众赞助支持他。目前,豆瓣收录西皮士的武侠风格音乐专辑有8个,曲目近百首。所得收入远超过他当公务员时的工资。
第二道门槛:足够宽广的商业平台。
成为一个数字游民,就意味着你将成为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商务经理,对于数字游民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商业化平台。
在今天,商业化平台几乎是社交网络或类社交网络的同义词,从海外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到国内的微信、微博、豆瓣,都是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大量潜在客户。
在美国,数字游民的另一主要族群―—艺术家、特别是画家、摄影师都是社交网络营销高手。
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艺术家们需要通过 种种复杂的渠道才能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如今,许多艺术家都将 Instagram作为自己 的“线上作品集”,他们在艺术市场上从被动渐渐转变为主动,自己担任着艺术品的创作者、经销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据《Hiscox在线艺术艺术品交易报告》 ,71% 的收藏者通过互联网购买艺术品。
这份报告发现,社交媒体不仅帮助重新塑造了互联网用户与艺术家、专业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在影响着艺术的传播乃至生产方式 。
在中国,类似微博、豆瓣、lofter也发挥着类似作用。
虫子(网名)在豆瓣九年就经历了“新用户-专业达人-创业者”的三次变形。2008年,为了给看过的书和电影分类,她注册了豆瓣,后来当兴趣聚焦在广告业时,又通过豆瓣的关联推荐搭建了知识谱系,后来又在兴趣小组里接触到了圈子里的专业网友,最后,在2011年创立了自己的小小广告公司。
“人五”在豆瓣上有4万多人关注,他的经历也颇为励志:从一个二本高校毕业后,专职从事插画设计,后来去了意大利留学,“上了豆瓣周年首页广告位,去年日历虽然画不好但卖挺好的,版税够我在欧洲一年生活费。”
当然,这听上去就像“别人的豆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闲逛和浏览是上网的常态,因为长期浮在信息平流层的表面,最终也失去深入的能力。这也注定了类似虫子这样的用户是少数的。但也印证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第三道门槛:足够强大的内心和自律精神。
成为一个数字游民,要求比“组织中的人”有更高的自律能力。
成为数字游民,你虽然可以摆脱恼人的办公室政治和大量无意义的冗长会议,但是你依然无法摆脱远程雇主那里的条条框框,可以说官僚主义无处不在,你逃离了集体,但依然还是仍受集体的一些弊端。
特别是对于那些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人来说,由于在异国常常给你回面临语言不通、不靠谱的酒店Wi-Fi、多变的形成的干扰,因此保持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ZestDesk创始人James Moore经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旅行,他认为在陌生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理健康,他给出的建议看上去还比较靠谱:
· 制定一个睡眠时间表,每天尽量在差不多的睡觉,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好不少于七小时;考虑到大部分数字游民都是跨时区作业,坚持做到这点十分难得。
· 创造一个宁静的环境,外出旅行最好带上耳塞和眼罩;
· 管理好焦虑等负面情绪,比如可以在睡前专门空出二十分钟来冥想。
· 除去心理健康之外,保持身体健康也相当重要。由于大量数字游民都是从事的脑力劳动,工作时大部分都需要对着屏幕,因此,一些久坐带来的疾病也不可避免。数字游民网站Proxyrack创始人萨姆克罗斯说,“桌椅糟糕的人体工程学和由此产生的背部和颈部疼痛影响了我的睡眠,情绪和生产力。”而他的解决方案,买一张便携式站立式办公桌,工作时尽量站着。
在生活方式上最好还是极简主义的信徒。做了三年数字游民的Cecilia Haynes在一篇播客文章中写道,成为一个数字游民的好处之一是,极简主义带来了巨大快感,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和一只钱包。
大势所趋,及早准备
即便再有吸引力,任何一种曾经令人怦然心动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保鲜期。
旅游博客作者Matthew Karsten,过去七年,在享受了边旅游边靠写游记博客赚钱生涯之后,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于是决定搬回到美国。为此,他专门写篇文章反思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困扰:
让人感到了寂寞,远离家人、错过无数的朋友聚会,旅行中难以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比起边旅行边工作,soho式的工作方式也许效率更高;
在50多个国家旅行之后,对于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
不过,真正让结束流浪汉生活,其实是他2015年在墨西哥遇上的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从而产生找一个窝、安一个家的冲动。而且他反复重申他并不后悔七年前的选择―—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另一位退出者Mark Manson 2013年写作《数字游民阴暗面》一文写道“经济学家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我看来,天下也没有毫无代价的自由生活。作为数字游民,我们只不过选择了另一幅更轻的枷锁而已。”
但未来更多人可能会主动或被动选择这样一副枷锁。
美国研究机构Gartner近日则表示,到2020年,人工智能将导致180万个工作岗位被淘汰,但届时也将创造23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被创造的新岗位,大部分要求更高的技能,更高的艺术感知和沟通能力,与当前数字游民所从事的职业类似。
与其踏上被机器奴役之路,不如早做打算。
一个美国青年的乌托邦实验
肯·伊格纳斯是“被失业”的。
2005年4月,他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毕业时,正值人生的最低谷,刚出校门就背负着巨额负债―—32000美元的助学贷款,一所普通大学的英文系本科文凭,让肯意识到,自己几乎难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唯一的就业去向是他假期打临工的一家建材超市,但这个21岁的年轻人已经受够了推车小工的活计。“回收推车、整理货架、倒垃圾、随时准备给顾客搭把手,没完没了,那才是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工作。
直到毕业时,“生在平常人家、长在郊区、接受大众教育”的肯才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每一个举动不过都是按部就班,读高中是法律强制要求,上大学是社会的主流,进入职场也是迫于经济压力,虽然拥有很多东西―—汽车、CD、数不清的衣服,却从来没能真正主宰自己的生活。
这次“顿悟”看上去如此套路。
长久以来,当肯转动自家卧室书桌上的地球仪时,他总是被其中一个地方所吸引,那里有茫茫雪原、绚丽的北极光和奔跑的麋鹿群。几乎在每个春天,肯都起意动身前往那里,但真到了暑期,在兼职还贷款、参加不带薪的实习刷简历,种种更为现实的考量面前,这个梦想一而再地被搁置。
阿拉斯加对于肯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总是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的向往,毫不逊于美女香车。终于在临近毕业前几个月,肯登上了前往阿拉斯加的飞机,在那片北极之地,他登上了5000多英尺的布鲁克斯山脉,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户外徒步、迷路。
所有有过户外登山经验的人,相信都有着和肯近似的感受:“登山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它能让复杂的生活简化,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竭尽所能,不轻言放弃。”这趟短暂的阿拉斯加之行,给了肯一股莫大的勇气,去挑战自己人生的大山,首当其中的是五位数的贷款。
如果把在超市的临工转正成全职工,抛去房租等日常生活开销,肯一年也省不出几千元,还债遥遥无期,可能真得还上20年。他需要的是一份低开销、相对高薪酬的工作,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几年内还清贷款。
前往阿拉斯加
肯决定和“按部就班”说再见。
告别按部就班的第一步是,在经历过25次拒绝后,他决定不再费劲给任何报社投简历了,直接去在阿拉斯加的冻脚镇,他发现在这个镇上的旅馆和餐厅打工时薪是他在超市拉推车的好几倍,而且还包吃包住,除了短暂的夏季外,地处北极圈的冻脚镇人迹罕至,当地几乎没有娱乐设施,常住人口为35人。
虽然与在超市推车类似,在北极圈打小工,同样属于“低技术含量、低责任要求”的双低工作,但这非常匹配肯想快速还款的需求。他在冻脚镇的第一份工作,是“北极山地探险游”旅行团的司机,最忙的时候,凌晨五点起床,忙到深夜十一点下班。
肯在旅行社收入的井喷,源自一次意外。一次,他拉着纤绳,协助六名游客上岸时,他一不小心被浪拍到河里,当天旅行结束时候,肯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小费。自那以后,肯每次在木筏接近岸边时,都会费劲地边拉着纤绳边大喊“大家都坐稳了,危险,然后“确保”自己被河水打湿。
在阿拉斯加的第一个夏天过去,肯不但还掉了四分之一的贷款,同时还攒下了3000多美元。在冬天来临之前,肯决定继续在这里呆下去,他成为了冻脚镇一家餐厅当夜班厨师。他的同事都是面带煞气、眼神冰冷的社会人,如同整个冻脚镇的冬天,“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特有的冷酷和肃杀”。
冻脚镇只有一个人让肯感受到人生应有的价值。“北极山地探险游”其中一个景点时智叟村,村里的民俗导游杰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每天都在劳动,每天都是假日”。他拥有全美最靠北的菜园子,还会捕猎、出售野兽的毛皮、下河打鱼,在旅游旺季还兼职当导游。肯羡慕杰克这种“独立、敏锐、坚强、健康”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一天到晚盯着道琼斯指数和失业率,忙着打卡上班、应付老板。”
在北极圈的长夜里,肯再一次感到了目标的虚无。在冻脚镇里打工的几乎都是背负重债的人,那也是肯正在经历的生活,而杰克的生活在肯看来最为自由,也是他理想的生活。在还清助学贷款后,肯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目标,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一个能让劳动变得有意义的方向标,让人生豁然开朗。
离开冻脚镇后,肯参加了一次加拿大安大略的独木舟之旅,一行五人效仿加拿大早期的船夫,用打火石和铁片引火,睡觉盖羊毛毯子和棉被,拒绝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杀虫剂、滤水器和野营炉,所行的独木舟也是遵循古法打造、不时漏水的桦木皮造。这趟1500公里的水上探险,让肯习惯了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劳动的节奏,却对文明生活愈发漠视。
在毕业两年后,肯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当初他之所以执意去阿拉斯加,是因为他想“跳出文明的圈子,看看真实的荒野”,看看“一个还没有被道路、人群、科技和垃圾淹没的天涯海角。”
但在冻脚镇的司机座里、在后厨的灶台边,肯并未看到完全真实的荒野。后来,当肯重返阿拉斯加时,他找了份北极巡山员的好差事,这份看似可以媲美澳大利亚的护礁员的工作,也有艰辛一面,得随身扛着60磅的背包,忍受蚊虫叮咬还有灰熊的袭击。
车居研究生
在北极巡山时,肯常和搭档静静地摇着桨,常常“几乎有一整天的时间任思绪随潺潺的水流四处蔓延。但思绪的河流总是不经意地围着两个漩涡打转。”
第一个漩涡是肯发誓不能再负债了。而另一个誓言是,肯给自己找到下一个人生目标,也是中国学生异常熟悉的选择——考研究生。
做下这个决定时已是2008年的夏天,肯在过去三年不但还清了所有贷款,还攒下了3500美元,也是他13岁当报童到现在第一次有了积蓄。肯另一个循规蹈矩的好朋友乔希,在一家贷款公司做销售,依然深陷债务和一堆不必要的开销之中―—水电费、健身卡、奈飞的会员费,牺牲的是自己的时间和自由。
肯收到了来自杜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为了能够在毫无负债的情况下从杜克大学毕业,肯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省去高昂的住宿成本,他花了1500美元买下了一辆1989年产的雪弗兰面包车,他准备住在车里。
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车轮上的瓦尔登湖,做起了杜克大学的梭罗,当然所有这一切必须悄悄进行。他拆掉中排车座以便安放床铺,一个行李箱和三层塑料抽屉整理柜架上野营炉,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在学校体育馆办卡用于日常洗澡,在图书馆看书的同时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充电,同时他还找了份校内兼职,给教授当助教,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开始,肯还很享受这种大隐隐于市的车居,他在车上写作、思考、阅读、反思,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那样,他期待孤独所激发的灵感。但一两个月之后,肯发现,他虽置身人群,却无法与任何一个人深交,孤独感阵阵来袭,他觉得还是需要交朋友,进行正常的社交生活。除了一只耗子和在户外俱乐部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肯以车为家。
杜克大学白人学生普遍家境优渥,平均收入在23万美元之上,为普通之家的五六倍之多。但冻脚镇和安大略漂流地经历,给了肯自信,他习惯不屈服于流行的风潮,不再盲从别人的价值观。“虽然杜克大学的人几乎不知道我住在车上,但我已经不在乎他们用什么眼光看我了。我自在地穿着从’救世军’买来的旧衬衫和褪色的牛仔裤,不再因此感到自卑、焦虑;我也不在乎头发是不是太长了,发型是不是很老土,只需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大方……”
期间,肯还去了趟瓦尔登湖,发现他的小木屋并建在森林深处,铁路近在咫尺,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他就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个人都能看到他。肯意识到卢梭的这场试验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每一个人。他联想到自己的车居生活,“车居试验的生活智慧,要是把它们憋在肚子里,谁也不告诉,似乎太浪费了。”
终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并经老师推荐在《沙龙网络杂志》发表后,车居生活终于曝光。为此他收获了近百个Twitter好友,甚至还收到了一些清一色来自同志们的求爱信。杜克大学也十分开明地处理了“车居事件”,学校给他提供了一块校内停车位,同时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毕业之后不得继续在校内停车。
肯也悟出一个道理:“住在车里并不意味着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只有走过自省的历程,才能看清长久以来困住我们的巨网是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肯把毕业后的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一如书名《车轮上的瓦尔登湖:从负债到自由之路》,2013年该书出版时,肯找到了自己对自由的定义:拥有改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