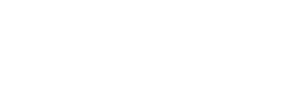No.58

【作者简介】科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MBA校外导师,关注数字化对人与社会的广泛影响,著有《单数社会》、《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工作中燃尽自我,以至于精力耗竭、消极厌世、效率崩塌,以及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工作、讨厌上班,希望一劳永逸的家里躺。
工作倦怠并非只是一个在办公场景才存在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员工自己的问题,它是由落伍的教育体系、畸形经济增长、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薄弱的社会支持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挞出的现代文明的伤疤。工作倦怠对于很多人来说,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设想,当你拥有一份大学文凭,在投出一百多份简历之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面试通知时,你会把原因归咎何处?是自己不够勤奋,还是家境平常无力“拼爹”,抑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脱节社会需求太多,还是经济形势太差企业缩招了?
生活在21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人,正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最具挑战的就业环境:
高校扩张,导致整个就业市场对学历要求的水涨船高,于是,博士毕业去当高中教师,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海归”回国成“海待”,这些十年前媒体曾经刊登的新闻人物,如今都不足以吸引记者们的关注。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是文凭去魅的过程。
毕业生可供挑选的职业,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随着自动化在各行各业的普及,从平炉工到胶片冲洗工,许多父辈们引以为傲的岗位,如今只存在于档案文字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想象力也日渐趋同和贫乏,从美国到中国,当一名大红大紫的视频博主,几乎成为了全球青少年共同向往的职业。这也是人类从生产社会走向消费社会的必然。
繁荣的服务业,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轻盈未来,从旅行预订网站的试睡员到外卖平台的配送小哥,在平台经济中,更多人奉献出的是比传统岗位更多的汗水和时间,以至于996成为今天科技行业的普遍的工作时制。相比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给你一个加班的机会,似乎也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烦恼。
相比70后、80后,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可能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代人,他们所处的中国早已不是“人口多、底子薄”,而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经济体,既是能够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产品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牌万般不愿开罪的世界商场。
更富裕的结果是,毕业之后,工作并非年轻人唯一的选项,于是间隔年也西风东渐,在中国流行开来,只不过人群从美国的高中生变成中国的大学生,从去公益组织做义工变成环球旅行,从思考人生的意义到享受人生的乐趣。
变味的不止是间隔年。在消费主义和互联网两股大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工作伦理已然分崩离析。不工作并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相反还是家境优渥、人心豁达的表征。在一个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传统的工作场景和内容早已发生变化,以至于人们对于工作的定义也在变化、工作的伦理也在蜕变。
工作和玩乐的边界从未如此模糊过。澳大利亚大堡礁守礁人早已不是最好玩的职业了。对着好山好水,人们也会生出好寂寞的哀叹。网游玩得好,可以晋升职业的电竞选手;喜欢写写画画摆弄视频的,则可以在各大内容平台从澎湃的流量中分得一杯羹;有把好嗓子的搞怪高手则可以在快手抖音上赚得盆满钵溢。
并不是“朝九晚五”“三点一线”才算是正经工作,一份工作干上几十年也不可想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在一份工作上的呆的时间普遍只有三到五年,一生跳上几回槽再正常不过,短暂、灵活、弹性取代了长期、稳定、刚性,成为我们现在主流的工作方式,一份工作已不足以成为我们身份的标识。
在这样一个处于变动不居的环境下,工作不再如同工业社会那样成为主宰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中枢,于是,那些说给劳动者的勤劳和奉献的劝告词,听起来都如此的空洞和欠缺诚恳。在一个数字化的消费时代,只有消费才会在我们的舞台中占据中央位置。
反正,无论是在格子间里朝九晚五,还是居家创业,今天的工作平台大部分都是对着屏幕,笔记本的、手机的、平板的屏幕,人生的悲欢离合就是在这一片又一片黑镜中起起落落、纵横捭阖。不知数百年后的地球人,再看待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会不会也是一脸困惑:他们为啥一天花上那么多个小时对着一块屏幕。
所以,如果你还拿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标准去评判今天年轻人的干劲,自然无法理解“三和大神”躺卧街头的闲散,也无法理解“窃格瓦拉”毫不掩饰对打工的蔑视,更无法理解为何啃老、蜇居、尼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工作人群为何越来越壮大。
这大概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今天,几乎没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罹患职场倦怠的人为何越来越多。公务员虽是铁饭碗,却并非最幸福的人群,在最近抗击新冠疫情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多一连工作数周;而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更是以社畜自居,凌晨一点的后厂村、中关村,许多栋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这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面。
勤奋并不总能带来财富,很多时候不过勉强度日而已,这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许多美国人一天做两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电;在日本,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但单位劳动报酬不及正式工,还会因为对于未来不确定,而自我延长工作时间;“世界是平的”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贫富差距的鸿沟在绝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在拉大,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更令人不安。
温柔的人总是伤痕累累,许多无辜的年轻人正在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后果,但职场专家们还是教导他们要继续提升自身技能、终身学习,适用职场的日新月异。然而,让人去适应机器又谈何容易。在无灯工厂的流水线上,忙碌的是工业手臂,工人们成为了照料他们的保姆;在装扮得像游乐园的科技公司办公楼里,程序员们扮演者21世纪建筑工的角色,为数字世界搭建框架;在一个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人在协调、适应机器,而非相反。
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对人异化的那一幕,焦虑、抑郁,倦怠不过是这种异化在我们精神面貌上的投射。
越来越细致的分工、越来越普及的自动化,在人们手头工作和交付产品之间树立起来一道又一道隔离墙,最终让人们看不清每一份具体工作的意义。无论是传统的科层制还是新近倡导的扁平化管理,本质上都无法缓解当下工作场景中年轻人所遭遇的意义虚无的精神危机。我们总得找到应对之道,于是,各种鸡汤文章走红朋友圈,冥想课程成为社畜们的新时尚,积极心理学成为当下热门显学,救赎之道层出不穷,但许多人还是被困倦怠的迷宫。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并非孤独地迷路。
在经历数十年的讨论之后,工作倦怠才被联合国正式认定为一种“职业现象”。
2019年5月2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将工作倦怠作为一种职业现象列入,但未将其列为一种医学病症。
世界卫生组织对工作倦怠的标准定义是:“工作倦怠是由未能妥善控制的长期工作压力造成的一种综合征。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感觉精力耗竭或耗尽;心理上与本人工作的距离感加深,或对本人工作感到消极或厌倦;工作效率下降。工作倦怠特指职业环境中的现象,不应用于描述生活其他领域的经历。”[1]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定义也引发了争议,联合国全球幸福理事会委员会成员珍妮弗·莫斯就认为该定义回避了导致雇员工作倦怠中的雇主的责任,她认为工作倦怠的根本原因在于雇主,只有从雇主那里采取行动,才有可能遏制倦怠蔓延的势头。[2]
早在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赫伯特·佛罗伊登伯格在自己供职的诊所中,发现包含自己在内的志愿者们普遍表现出了极度劳累、头痛失眠以及消极易怒等现象,他将这种如同精力燃尽的现象命名为“倦怠”。1974年,他在《社会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人事倦怠”的文章,采用“倦怠”一词来描述工作中的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组负性症状,如长期的情感耗竭、身体疲劳、工作卷入程度降低,对待服务对象不人道的态度和降低的工作成就感等。[3]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拉奇在后来的研究中,把佛罗伊登伯格提出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作倦怠,并将之定义为,“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体(玩世不恭)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4]
后来,马斯拉奇还编制了鼎鼎大名的“马斯拉奇工作倦怠量表”,试图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等三个大方面量化分析职场人士所经受的“职业倦怠”量值,进而评估劳动者的心理疲劳状态。具体看,情感耗竭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乏不堪,精力丧失;人格解体指个体对待服务对象负性的、冷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个人成就感降低指个体的胜任感和工作成就的下降。
四十多年来,有关工作倦怠的研究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职业健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不过,专家们虽然普遍认同这是当代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迟迟未列为疾病,直到前不久才达到共识。
工作倦怠是从个体的心理特征中反射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由于现代社会宣扬独立与自我的价值观,比较重视人们在物质上的成功,比较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具体到工作上,就是强调个体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而无视个体工作中体验到的孤独与压力,个体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难以释放消极情绪,也难以关注他人感受或其他事物,所以就容易引发倦怠感。
(1)
不分国别、职业
如同新冠病毒一样,倦怠自由穿梭在世界各个国家、阶层和工作岗位之间,无需护照、无需许可。
在21世纪,工作倦怠的范围,早已经超出了护士、医生、服务员、律师、教师等马斯拉奇在早年界定的那些容易患上职场倦怠的职业,更是超越了白领和蓝领的楚河汉界,也超越了职场中的等级森严的不同层级,俨然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2004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持完成了在中国第一次针对工作倦怠的大型调查,最终形成《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结果》报告对外公布,称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工作倦怠现象正在袭扰中国。当年的调查发现,有70%的被调查者在“马斯拉奇工作倦怠量表”的三项指标中的一项上出现工作倦怠,处于轻微工作倦怠;有39.2%的受访者在两项指标上出现工作倦怠,处于中度工作倦怠;13%的受访者在三项指标上均出现工作倦怠,处于高度工作倦怠。[5]
在大洋彼岸,美国职场人的压力也不容小觑。在2015年,德勤对1000名全职美国专业人员进行的外部市场调查发现,就已有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在当前的工作中经历过不同程度工作倦怠,其中一半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工作倦怠。将近70%的专业人员认为其雇主没有为防止或减轻组织内的职业倦怠做足够的工作。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未提供任何计划或举措来防止或减轻职业倦怠。[6]
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工作倦怠症是荷兰排名第一名职业相关的疾病。从2007起,荷兰有工作倦怠症状的人数逐年攀升,直到2014年间总计有14%的劳工有此病症,约有5%的劳工因此在家休养,每七人中就有一位劳工过劳,因工作倦怠症请假缺席的日数高达242天,造成约1.8万亿欧元的损失。
在德国,德甲球队沙尔克04的教练兰尼克在2011年的辞职,引起了一场关于工作倦怠的大讨论。德国《图片报》报道,现年53岁的兰尼克是因为患上“工作倦怠症”,身心疲惫,无法再继续执教。兰尼克本人也坦言“需要一段休息时间”。[7]
根据职业风险评估公司Technologia的研究,12%的法国职场人士(总数约为320万人)面临筋疲力竭的风险。这项研究认为,由此产生的后果不仅对个人非常危险,还会给整个国家带来财务危机:Technologia的研究估计,法国每年因为工作压力产生的社会成本在20亿至30亿欧元之间。而根据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最新测算,美国的职场压力则会每年额外创造多达1900亿美元的医疗成本。
在韩国,每十个未婚男女中的有八人经历过工作倦怠,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体会到了由此对恋爱所带来的诸多困惑。对于经历过职场倦怠的未婚男女中42%的人若面临提前下班机会时他们的首选是“回家休息”、其次是选择“与朋友或爱人见面”(31%)、“看电影等文化生活”(17%)、“运动”(6%)、“其他”(4%)。[8]
日本国立循环器官病研究中心与九州大学在2014年联合公布,日本四成中风诊疗医生因长时间工作及睡眠、休息不足,染上“工作倦怠综合征”。该研究对2564名脑外科以及脑神经内科医生进行了专业测试。结果显示,41.1%的医生符合“工作倦怠综合征”的标准。具体而言,每工作10个小时,得“工作倦怠综合征”的人数比例就会增加12%,而每天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相应的比例就会降低20%。根据本次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表示,增加医生的睡眠时间和休息天数,有望减少医生得“工作倦怠综合征”的比例,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9]
(2)
“铁饭碗”也倦怠
工作压力不仅普遍存在于企业,就连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的工作压力也难以幸免。
2012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调研组针对价值观、心理健康、幸福感、工作倦怠感和角色压力等5个方面的问题,先后在山东、福建、陕西、湖北、黑龙江、安徽、湖南、浙江、山西、云南等10个省份,对当地党政部门中在职在岗的县处级以下(含县处级)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10],调查规模累计2482人次,调查发现群体心理健康总体良好,在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满意度体验,但是他们同样也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得分随着代际而递减:“50后”为8.26分、“70后”为8.18分、“60后”为7.97分、“80后”为7.56分(12分为满分)。调研组分析认为,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于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这次调查还有一个发现,79.89%的基层公务员或多或少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个人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心疲惫、工作投入低、不良的服务态度和人际关系等状态,它是任何类型的职业群体都可能隐含的职业症状)的现象,而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的基层公务员比例为6.40%。调查组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倦怠情况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检出率最高的因素是成就感低落(51.74%),人格解体因素的检出率居中(37.48%),情感耗竭因素的检出率最低(18.83%)。
调查报告建议,“成就感低落”因素的检出率最高,这提示我们对于公务员管理和任用的改革,一方面要加强各类岗位的轮换,另一方面也要给予基层一线同志一定的工作空间,完善进出机制和奖惩机制。通过调动基层公务员自主工作的积极性,帮助其实现个人价值与事业发展的有机结合,从而提升工作成就感、减少不良情绪、改善工作态度、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过职业倦怠与员工所处级别也有一定关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3年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到2013年,职场人主要表现出视疲劳、容易感到疲倦和记忆力下降等身体不适症状。在心理感受方面,层级越高,心理越健康、抑郁倾向越低、工作耗竭越低。高层管理人员的心理最为健康。
(1)
从童话王国到世界工厂的压力之旅
“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请了一年多病假,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老记不住事儿。”[11]面对BBC记者时,纳塔莉·索维耶里忍不住吐糟自己的工作。
索维耶里1994年出生,家住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曾在一家小型初创企业担任营销经理,她的标准工作时间是“朝八晚五”,不过加班是常事,晚上还得回复工作邮件。2017年,她身心俱疲,被迫辞职。
这可能让中国的年轻人感觉有点矫情。毕竟瑞典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480天的带薪育儿假;15个月之内最多364天的带薪病假,病假工资为正常工资的80%;除了公共假日,瑞典公司还必须给员工放至少25天年假,员工在7-8月间可以连续休四周假,去避暑别墅或阳光灿烂的南方度假。和许多国家并不承认职业倦怠属于工伤事故不同,在瑞典,被诊断患有职业倦怠的人通常可以拿到约80%的薪水,最高为每天774瑞典克朗,即使生病也不会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但经济补偿并非万能之药,对于倦怠之苦,正常人难以感同身受。BBC的报道援引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精神病学家玛丽·阿斯伯格的话说,“倦怠症状因人而异,但通常包括长期持续的压力,可能表现为严重的疲劳、焦虑、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其他认知障碍。一旦患病,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大脑不能正常运转,你就很难正常工作。”
索维耶里的情况在这个外人看来无比幸福的北欧童话王国里并非个案。根据瑞典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职业倦怠”是2018年瑞典人失业的最常见原因,在所有年龄段的劳工社保案例中,这类疾病占20%以上。在瑞典,自2013年以来,25岁至29岁人群的患病人数上升了144%。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感到疲惫。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人们在职场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在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升至世界第一的五年后,根据办公方案提供机构雷格斯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12],中国内地上班族压力的上涨已位列全球第一。
从2012年4月开始,这家调查机构对全球范围内8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6万名职场人士进行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中国内地上班族认为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去年更高了,这个比例位列全球第一。位列第二的是德国人。在中国内地,上海似乎成为“压力之都”,受访的上海在职人士中有近 80% 感到压力上升,北京的比例是67%,香港有55%的上班族表示所承受的压力高于去年。这份调查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把工作视为压力主要来源的受访者比例比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要高。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调查显示,小企业员工比大企业员工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客户的压力。
与上海经济往来密切的台湾地区,那里工作族也不轻松。据新华社报道[13],台湾人力资源机构1111人力银行在2017年7月30日发布针对岛内“60后”“70后”和“80后”上班族进行的“跨世代压力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6%的台湾上班族坦言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大,其中薪水低是主要原因。上述调查显示,受访者自评身心压力指数平均值为63,有21%的受访者压力指数高达80以上。整体而言,男性的压力值高于女性5个百分点。工商业服务、媒体及出版、民生服务为压力最大的三个行业。
健康调查也能反应出中国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2015年,平安健康险和零点咨询为时半年、向中国15个城市和8个行业的499位资深人力资源经理和2099企业员工的调查显示[14],中国企业员工健康状况堪忧中国企业员工Vitality年龄(Vitality年龄是指:通过员工的个人行为及身体状况计算其Vitality 年龄,有助于员工了解其健康情况及影响其健康的关键因素。)平均比真实年龄老5.7岁,近60%的人员患有各类慢性疾病,工作压力是健康风险首要诱因。
2012年,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对5609人的调查显示,身体不健康症状明显(中度以上)的人群占到了调查总数的1/3,其中,身体症状情况较差的是26-35岁群体,正是职场人群的中坚力量,长期的忙碌和压力导致个人身体方面的症状也会比其他人群更多。
(2)
压力如何诱发倦怠?
大量研究表明,工作压力已成为成年人压力的主要来源,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压力已经逐步上升。美国职场心理咨询机构卡尔默(Calmer)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超强压力都会导致倦怠,倦怠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经历系列压力的叠加,往往会经历五个阶段:[15]
①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蜜月期,往往是由于人们刚刚接受一项新任务,打算雄心勃勃地大干一场,因此对领导作出了较高的承诺;
② 第二个阶段是压力发作期,人们发现乐观情绪在逐步衰减,身体、心理上压力开始增大,可以表现为情绪焦虑、躲避决策、健忘、疲劳、食欲大幅度波动、无法集中注意力、易怒、睡眠质量下降、晚上磨牙增多、缺乏社交、甚至头疼、心率不齐;
③ 第三个阶段进入慢性压力,相比上一个阶段,症状变得更严重了,包括常常有愤怒或攻击性行为、冷漠、早晨持续疲倦、变得愤世嫉俗、性欲降低、工作拖延、迟到、项目交付一再延期、酗酒、咖啡喝得越来越多、甚至怨恨。
④ 第四个阶段进入符合医学诊断的倦怠标准,典型表现为逃避工作、慢性头疼、内心感到空虚、慢性肠胃问题、对工作和生活都感到非常悲观,渴望“退出”社会、持续自我怀疑、渴望远离同事、朋友、家人,甚至进入社交隔离状态。
⑤ 第五个阶段是习惯性疲倦,这意味着倦怠已经成为你日常的一部分,此刻的问题已经会超出倦怠,比如陷入慢性抑郁症、慢性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
虽然各个行业各有差异,但压力引发工作倦怠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体在工作中被要求的大量付出,比如过大的工作量、比较恶劣的工作条件等;二是在上述情况下,企业给员工提供的工作资源匮乏比如福利待遇、发展空间、工作参与性等,而工作要求又比较高时,个体就容易产生工作倦怠。上述两种因素都会令人产生压力,从而成为倦怠的重要诱因。像任何重大健康问题一样,职场人越早认识到倦怠综合症的症状,就越有机会康复甚至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招聘服务商前程无忧曾经在网站上分析过这样一个案例:
“小张是一名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本来可以有很多发展方向,可是最开始的择业却坎坎坷坷,甚至在一个月内主动放弃了两份工作。最开始小张通过父母的关系进了一家银行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起码日常生活可以衣食无忧。可是毕竟是新人,小张一开始就被安排到柜台熟悉业务,如此日复一日地收钱、点钱,对他来说太枯燥了。作为刚毕业的择业人,小张更向往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手拎笔记本的白领们,于是,在银行工作还不到半个月,小张就辞去了这个比较稳定的“金饭碗”,跳槽到一家公关公司。但是进了公关公司,小张依然只能从一些繁杂的琐事做起,譬如打字复印、接待、端茶送水,新工作的美丽憧憬渐渐在小张的心中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像第一份工作那样的焦虑和烦躁。终于有一天,小张又无法坚持上班了,不到两个星期,他再次放弃工作。从公关公司辞职后,小张对自己是否能够适应正常的工作产生怀疑。不管什么工作都同样枯燥乏味,不能提起他半点兴趣。”[16]
人力资源专家分析,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中,跟小张相同的例子不少,这些恐惧上班、害怕工作的现象并非个别,甚至有的人一上班就想要什么时候辞职,这其中也不乏在职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从业人员。
据此,专家给出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正确自我定位:患有工作恐惧症的人总是过于重视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总是想到“我想做什么”和“我喜欢做什么”,却很少考虑“公司需要我做什么”和“这份工作本身要求我做什么”。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才使这些毕业生在工作中常感到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进而开始怀疑工作本身的价值,所以恐惧上班或频繁跳槽;二是阶段性目标:毕业生要学会确定阶段性目标,在平时的工作中有意识地训练自信心,学会自我调节,提高抗挫折能力。毕业生在校期间应该参加学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在学校就开始进行“预防”。对于已经踏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如果碰到问题,则完全可以和公司的人事部进行沟通。
但知易行难,“厌班”情绪在职场人中就像感冒一样常见。
脉脉数据研究院在2017年11月发布的《职场人厌班情绪调查报告》显示,有四成职场人有严重的上班恐惧症,这类人群被报告方称之为重度丧班。另三成职场人属于中度丧班,只有27%的职场人轻度丧班或没有丧班症状。看来,依然有三成的上班族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 丧班族的典型特征是情绪不稳定,爱拖延,暴饮暴食和想辞职。有不到一成的职场人,常年处于重度不开心的情绪中。建议重度丧班族适当咨询心理医生,多与家人朋友沟通,舒缓压力。这份报告显示,显示,四成多的上班族坦诚表示因为赚的少不想上班,三成表示原因无他,纯粹不想上班,还有三成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内容与工作伙伴让人没有上班的欲望。[17]
除了工作的刚性压力之外,导致职业倦怠还有很多个人的主观因素。
2018年盖洛普(Gallup)在全球范围内对7500名劳动者的研究表明,由个人原因引发的倦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① 不合理的时间压力。对很多人来说,缺乏时间是造成倦怠的主要原因。美国心理学网站“拯救时间”(RescueTime blog)通过对500人的调查发现,在许多公司中,人们将80%的时间都花在开会,打电话和回复电子邮件和及时通讯消息上,而留给员工很少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必须完成的所有关键工作。根据多项研究显示,工作中持续的沟通实际上会降低我们的生产力。相反,最具创造力的团队会在协作和隔离之间交替。[18]
② 对工作责任和期望不明确的压力。你是否清楚自己的优先事项和职责?如果每年你所追逐的工作目标都在变动时,你就很容易变得精疲力尽和沮丧,特别是当你遭遇一个缺乏大局观、战略思维、决策多变的领导时,这种工作责任和期待压力会变得更大。不幸的是,盖洛普在2018年所作的一次“美国工作场所状况”报告显示,只有60%的工人说他们清楚地知道每天老板对他们的期望。
③ 缺乏和上级沟通的压力。根据盖洛普(Gallup)2018年的一份报告,在经理的大力支持下感到疲倦的可能性降低了70%。另一方面,优柔寡断,疏忽大意或积极进取的经理会使您感到与世隔绝,沮丧和愤世嫉俗。
前面提到瑞典姑娘塞西莉亚·艾克斯兰对BBC记者说,销售工作确实累人,但在业余时间锻炼和“完成任务”的压力也是导致她疲惫的重要原因。 “你需要健康,需要健康的饮食,需要放松,也需要‘就位’。”她说,“我基本上没有休息过,这让我筋疲力尽。” 一项调查显示,瑞典人的运动量超过除芬兰人以外的所有欧洲人,近三分之一的人每周锻炼5次以上。研究证实,运动能促进心理健康,但身体已经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还过量运动,可能适得其反。
疲惫不仅是对长时间工作的反应,竞技游戏或熬夜刷剧、一刻不停地刷Facebook、Twitter、快手、微博也会导致疲惫,因为大脑无法区分工作和其他非工作任务。
看电视是否真的有利于放松的问题,《科学美国人》杂志在2002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的研究表明[19],当我们坐在屏幕前,像僵尸一样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大脑中高功能水平的活动会暂停,比如说,掌管分析推理的新皮质会沉寂下来。与此同时,脑部最大的皮层组织——视觉皮质会高度活跃。于是,大脑进入了某种介于休息与工作之间的奇妙状态——神经元仍在激活,但大脑却什么都不干——它摄入了大量信息,却不去处理,所以大脑并未完全休息,但同时也没有干活。
社交媒体也容易引发倦怠并带入到工作之中。全球领先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Gartner于2010-2011年间对11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6295名年龄在13~74岁之间的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显示,31%的社交媒体热衷者回应说已开始厌倦社交网络,24%的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喜爱的社交媒体站点的使用频率已低于注册时,这种趋势表明社交媒体的早期采纳者已开始出现社交媒体倦怠。
年轻人的闪辞、慢就业,也与一个广泛存在的职业现象——工作倦怠有关。
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德勤的一份报告中提到,84%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在目前的工作中经历了职业倦怠,而所有受访者中的这一比例为77%。近一半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感到精疲力尽,而所有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42%,表明包括95后在内的千禧一代的工作倦怠程度要高于平均水平。[20]
相比上一代人,千禧一代更容易遭遇工作倦怠,压力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普遍现象。
千禧一代也源自西方的话语体系。西方社会普遍将21世纪称为千禧年,意为耶稣再次降临的美好时代。千禧一代,也称为Y世代或Y世代,是X世代和Z世代之后的人口统计群体。人口统计学家和研究人员通常使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出生年份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作为出生年代。关于千禧一代的具体断代,在美国,不同的机构、学者所给出的年代区间都不一样,但是都遵从最原始的对于千禧一代的定义:在千禧之初(2000年),逐渐成年的一批人。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称“千禧一代是有史以来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 [21]在英国,2014年,在18-34岁的千禧一代中,有近三分之一(29%)的人已经持有学位证书。当 X一代在相当年龄时(2000年),只有24%的人持有学位。假设千禧一代遵循与 X一代相似的轨迹(34%的人在2014年之前获得学位),大约有四成的千禧一代将持有学位,使他们成为我们所见过的最受教育的一代人。
但受教育程度高的另一面是,长期教育的成本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教育变得更加昂贵,而千禧一代的学生毕业时比他们之前的几代人负债更多。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具有学生债务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成年人的家庭的资产净值中位数(8700美元),相当于没有学生债务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成年人的家庭的资产净值中位数(64700美元)的七分之一。 [22]
千禧一代并不比上一代人更懒惰,但生逢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就业岗位外移,被新技术所取代,因此,固然他们的工作意愿并不比上一代人更弱,但他们面临的就业竞争可能也是空前的。2019年初,科技媒体BuzzFeed刊发一篇长文,直呼美国千禧一代为“倦怠的一代”。由于工作时间更长、工资停滞不前,千禧一代比其他几代人更容易感到倦怠。这篇文章作者美国安妮·海伦·彼得森引用自身经历痛陈这一代人的“过劳”:
“要准确地描述千禧一代的过劳就要承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角色的多重性——我们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父亲母亲或知识工作者,而是所有这些社会角色的总和——同时承认现状:我们负债累累,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更多而工资更少且缺乏保障,我们苦苦挣扎想要达到和父母辈一样的生活水平,在身心健康都不稳定的状态下前行;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只要我们更刻苦,我们的日子会兴旺起来。那根吊着我们胃口的胡萝卜,就是梦想有朝一日我们任务清单上的事情都能办完,或者至少不会多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23]
布鲁金斯学院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千禧一代将如何颠覆华尔街和美国的所有公司》报告中指出,“将近三分之二(64%)的千禧一代说,他们宁愿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年薪四万美元的工作,也不去做他们觉得无聊的年薪十万美元的工作”。
中国的千禧一代也是肩负重任的一代。
埃瑞克·费什曾在中国呆过七年,从2007年到2014年,他先是在清华大学念新闻学研究生,然后,同时还担任过《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他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千禧一代》一书中写道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观察,他们既有着美国人不必担心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也有与发达国家的同辈人类似的问题,比如飙升的房价和就业机会的缺失:
“中国的‘千禧一代’在他们小时候,总被灌输这样的观点,只要好好学习,未来就是一片坦途。这对他们的父辈来说,的确如此,当年的大学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然而,时过境迁,现今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依然较难找到工作,就业市场并不太乐观。不过,尽管压力大,但这些年轻人依然很乐观,非常难能可贵。面对这些压力,‘千禧一代’正在变得越来越需要寻求精神慰藉的来源。他们往往不排斥倾诉自己的精神压力,也乐于寻找帮助和指导。”[24]
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长迟缓的欧洲,千禧一代更加迷茫。
2008年全球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千禧一代首当其冲,他们要承受诸如临时合同制的低薪工作,不断上涨的房价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等。在西班牙,年轻人感受到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生活压迫尤其明显。与X一代(1966年至1980年出生的一代)相比,同龄的千禧一代在30岁至34岁这个年龄段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了30%。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五年后,即2013年,西班牙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6%。在过去的十年中,西班牙年轻人长期失业率达到了过去的五倍。由此导致78%的人在30岁时仍与父母同住一起。
马德里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及马德里应用经济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第一代无法保证自己能获得比父母更好的生活的一代人。我们在2014年做了一次对比研究,比较了这代年轻人和前几十年的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我们不得不追溯到80年代末才能找到和如今类似的生活状况。”[25] 拉莫斯在她参与写作的《看不见的墙》一书中探讨了西班牙青少年成长为独立成年人的障碍。她认为,(西班牙)千禧一代所面临的经济限制正在拖慢他们跨越人生重要里程碑的进程。人生的重要转变,如成为父母养儿育女,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停滞不前。2018年,西班牙创下了40年来最低的出生率,即平均每位母亲生1.3名子女。1972年时的出生率是每位母亲2.9名子女。
德勤在2019对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3416名千禧一代(此处指1983年1月至1994年12月期间出生的人群 )以及1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9名Z世代(此处指出生于1995年 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的人群 )展开了调研发现,虽然全球正处于经济扩张时期且产生了大量机遇,但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自己的事业、生活乃至周遭一切都存在焦虑和悲观情绪,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26]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千禧一代称比特币是一项积极的技术创新,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比特币比银行更安全。[27]
报告分析这与千禧一代所处于历史周期有关,千禧一代步入职场之时正值经济危机爆发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显示,千禧一代的财富要少于1989年至2007年任何一年的同龄人。2008-09年的经济危机对千禧一代的打击尤其严重。2016年,20至35岁的家庭财富中位数比2007年的同类年龄组低约25%;[28]另一方面,大量的Z世代人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后危机时代度过,在经济衰退时期进入职场会对后续的薪资和职业道路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相比前几代人,他们在相应年龄阶段所获得的实际收入和积累的资产较少,而负债水平则较高。该等累积效应对千禧一代的财务决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德勤调研发现,千禧一代对企业的评价持续走低,认为企业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受 访者比例在2018年跌至61%,此前四年一直保持在70%以 上,而今年的这一比例更是下滑至55%。新兴国家千禧一代对企业的评价对这一趋势起到了助推作用。新兴国家对企业持好评态度的受访者比例从两年前的85%降至如今的 61%。成熟市场在同一时期的这一比例也下降了16个百分点,跌至50%。
千禧一代与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人)对情绪衰竭的反应有所不同(情绪衰竭通常是倦怠的第一阶段)。当感到情绪疲惫时,千禧一代相比婴儿潮一代更容易感到不满且想要离职。49%的千禧一代表示,如果有选择,他们将在未来两年内辞去现职,这是德勤所有相关调研中的最高比例。而在我们2017年的报告中,这一比例为38%。这并不是无聊的威胁:表示将在两年内离职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表示在过去24个月内有辞职行为。这对希望培养稳定员工队伍的公司是一大挑战。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千禧一代也在重新思考着对人生成功的传统期望是什么。从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来说,什么样才算成功,可能都在被颠覆、被重新定义。
身处数字时代的一大不幸是,人们太容易找到你,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7×24小时在线,老板、同事很容易在下班后继续在微信、钉钉、邮件上处理工作,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倦怠。
苹果无疑是最早一批“永远在线”的推手。从一系列产品的设计就可以看出来,乔布斯并不想让他的客户关闭电子设备。他在iPod上第一次消灭了电源键,Macbook Air的电源键也设定成休眠功能,iMac的电源键藏在机器后面和底壳浑然一体。
《乔布斯传》里提到了乔布斯的一个偏好,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专门设定这样一个流程:按下去——等待关机——再见,电子产品就应该随用随开。虽然乔布斯从产品的极简设计和出色用户体验的角度,消灭了用户使用手机时的关机习惯,但同时也助长另一种灾难性文化的到来。iPhone 4上市一年后,就在美国官网推出全天候网聊(24×7)客户支持,以应用人们全天候的使用手机的新形势。
在苹果推出全天候网聊这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莱斯利·佩洛也意识到了智能手机对办公文化的革命性颠覆:职场精英们开始习惯凌晨给同事发电子邮件,同时期待在凌晨三点收到回复。以防错过公司的重要邮件,不少人开始把智能手机放在床头,与手机同枕共眠。于是她写了一本书《与智能手机共眠——打破7*24小时习惯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呼吁人们改掉24小时在线的坏习惯。
佩洛在书中还提到了这么个例子,美国芝加哥公关机构Empower Public Relations的CEO萨姆·查普曼(Sam Chapman)表示,他过去曾出现幻听,总感觉手机在震动,而且会经常在半夜查看自己的黑莓手机,收发邮件。他的睡眠质量很差,早上起床总会感到精神萎靡不振,他认为,自己“手机成瘾”了。他表示,“我希望确保,我的员工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为此,查普曼制定了了一个所谓的“黑莓管制政策”。工作日时,他和手下20名员工们从下午6点开始会将手机关闭,直至第二天早上6点;到周末时,他们会将所有与工作有关的设备全部关闭,鲜有例外。查普曼称,“休息好就能工作好。”他在旅行中也会继续遵守该政策,并表示,这个政策提高了公司的生产力。
但Empower Public Relations毕竟少数。如今,永远开机、永远在线的智能电脑也上市了。
在德国柏林IFA 2019大展上,联想集团推出了一款可以永远在线的笔记本电脑,并提出了一个目标:10%以上的电脑提供AOAC(永远开机、永远在线)的功能,并配备自然语言交互的人机交互模式。据报道[29],在AOAC(永远开机、永远在线)状态下,如同智能手机一样,电脑系统将以超低功耗运行,并仍与网络连接,从而实现满足用户持续接收文件,下载资料等需求。电脑上智能摄像头可以仅通过用户的一个眼神或一个转头动作就将选定的内容从一台显示设备移动到另一台显示设备上。联想集团用户和客户体验业务副总裁Dilip Bhatia表示: “下一代职场人士是由互联网伴随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要求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他们通过推动技术在商业环境中更快地普及,从而模糊消费产品和商用产品之间的界限,利用科技实现工作与生活的高效融合。”
从苹果到联想向消费者发出的用不下线的信号,一定是洞察到了当下商业的新常态。如同联想这位高管所说,我们身处一个大融合的时代,消费设备和工作设备、工作和生活的边界都在迅速模糊,从智能手机到电脑,24小时不下线正在成为新常态。
下班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国际招聘顾问公司米高蒲志(Michael Page)调查1328名新加坡本地专业人士在上班时的快乐和专注程度,结果发现[30],下班时间也回复工作电话和电邮的受访者当中,84%表示自己有责任和公司保持联系。
(1)
错误的新职场政治正确
① 鼓励超时工作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职场政治正确。
著名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Future Workplace的研究主任Dan Schawbel认为,企业总是奖励工作时间更长的员工,并取代那些没有承担更多工作量的员工,这是造成职业倦怠的系统性问题。咨询公司Family Business Institute的总裁韦恩·瑞沃斯(Wayne Rivers)表示,许多企业“看重那些能在凌晨1点接电话的员工。”在多数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按照规定以避免过劳和倦怠”由员工自己决定。
超时工作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统计,全球有超过4亿员工每周工作49小时及以上,在全球近18亿就业人口当中,此比例不小。即使是企业家埃隆 · 马斯克( Elon Musk),近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到自己47岁生日只能在工厂里熬通宵时,也颇为感慨:“没朋友,什么都没有。”与平时每周工作120小时的日子没什么区别。他说:“我彻底牺牲了和孩子们、朋友们见面的时间。”
② 零工经济更是永远在线的重灾区。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伍德(Alex J Wood)负责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为科技公司写代码、编辑博客、建设网站,或是管理社交媒体的年轻人,受困于激励员工超时工作的系统,直接导致了持续过度疲劳。一位被调研者告诉伍德,“我这么穷,有人要给我钱,那为什么一天不花个18小时干活呢?”零工经济的很多领域似乎都出现了这种过劳模式。美国有报道称:一些网约车公司的司机为了充分利用车费上涨的机会,每天驾驶时间达到20小时。在英国,在议会调查后,优步(Uber)将司机持续使用网约车服务的时间限制为10小时。对于绝大多数弱势的自由职业者,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大概没机会结束长时工作导致效率减弱的恶性循环。正如伍德所言,潜在问题是“客户能影响打零工者未来的收入”,而这些人却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③ 硅谷也把随时在线的文化推向高峰。
据美国科技媒体Buzzfeed采访的一位 Uber 雇员称,在公司快速增长期,Uber员工必须随叫随到,有时晚上甚至会被打搅上百次。即使是已经做好在新创公司打拼准备的员工,也会被这种随叫随到的模式弄崩溃“有时我周末也能收到信息,电邮更是会在晚上11点不期而至。如果你不在30分钟内作出回复,可能会断了整个团队的思路,因为至少有20人是在一个链条上的。”
Uber的永远在线,也源于资本的急功近利、市场竞争的血雨腥风。2015年5月,一位24小时值班的工程师没能及时处理主数据库的问题,随后Uber在全球的运营团队都受到了影响,驾驶员无法登陆Uber平台,运营人员也无法回应乘客的求助。当时,Uber刚刚拿到500亿美元的估值,一次全球运营大混乱绝对是大事故,公司 CTO Thuan Pham 直接在公司群发了邮件,让员工警惕起来别再犯错误。“值班的工程师收到了3次提醒居然都没反应,这绝对不可接受。”Pham 在邮件中愤怒的写道。“我们正在做调查,看看这位工程师到底为什么会错过警报。”据悉,看到这封邮件的员工超过3500人。即使两年后,这封邮件依然让许多员工记忆犹新,一位前员工将其称为“恐怖文化”。
在中国,下班后回不回工作微信、钉钉也引发争议。据《工人日报》报道[31],2017年7月,王女士进入宁波某饮品店工作,担任店长职务。2018年7月2日22时23分,王女士所在单位负责人在工作微信群上要求在10分钟内发当月营业额,不发就辞退。王女士因怀孕较早入睡未及时回复,10分钟后,单位负责人在微信工作群上通知王女士已被辞退。第2天在王女士去店里上班时,单位告知其已被辞退,并拒绝向王女士支付上月的工资。尽管在宁波市总工会的帮助下,王女士成功维权拿到了应得的赔偿金,但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网络热议却未降温:下班后,面对这种“紧急工作微信”回还是不回?职工能否拒绝?下班时间回复微信算不算加班?
《工人日报》援引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唐毅观点称,理论上职工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至于是否算加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在很多单位实行加班审批制,只有经过公司审批的延时工作才属于加班。但如果公司在职工下班后布置工作,且明确要求职工在明天上班之前完成,这种要求,显然需要职工利用下班时间完成,应属于加班。
(2)
健康为之埋单
① “永远在线”的工作模式未必高效。
贝恩咨询公司的高管埃里克·加顿指出:“当员工的生产力不尽如人意之时,罪魁祸首通常是企业,而非员工。”贝恩公司观察了一些倦怠率偏高的企业,发现有三个常见的弊端存在:过度合作、时间管理不够规范、能者过劳的倾向。这些问题不仅占用了员工原本用于完成复杂任务或者想法的时间,还大量消耗了员工用于恢复精力的休息时间。
② 但对健康的危害不言自明。
2010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32],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另有统计显示,在30岁至50岁英年早逝的人群中,95.7%死于因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数据显示,日本每年有上千人因“过劳”死亡,美国每年也有上千白领患上“压力恐慌症”。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每周工作21~40个小时的女性相比,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女性所需要的怀孕时间要长20%;超长工作造成的“心理包袱”还会给家人带来影响:没空陪孩子、夫妻交流少、父母没空管等,甚至导致家庭矛盾。
伦敦大学基维马基博士的一项研究显示[33],每周工作长达48小时比35到40小时中风的风险增加了10%,工作长达54小时,增加25%,如果超过55小时,就会增加33%。在每周工作30到40小时的组群中,每1000人中只有不足5人中风。在工作55或更长时间的组群中,每1000人里中风人数增加到6人。这一研究成果刊发在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提示人们遵循朝九晚五的惯例,否则中风的机率就会增加。
Uber的这种“随叫随到”与准时上下班是两码事,我们的身体对这两种情况的反应截然不同。2016年一项研究发现[34]:早晨随叫随到者的皮质醇(又译为可体松,人体应付压力的激素,因此也称为压力荷尔蒙)水平比不需随叫随到的员工升得要快,即使他们可能一直到晚上都没工作可做。这种压力荷尔蒙一般在人们刚睡醒时达到峰值,然后慢慢减少。但科学家认为,日常压力会以各种方式让周期紊乱:比如你预计今天会很紧张,那激素就会上升(研究人员觉得打零工就是这样),如果你长期压力都很大,这个激素就会一直偏高;如果在长期压力后你开始经历“倦怠综合症”,那这个激素就升不上去了。结果是,“随叫随到”的人发现越来越难“从心理上区分工作和非工作”,很难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研究人员称之为“控制能力”。换句话说,员工并不觉得“随叫随到”的时间真的是自己的,他们的压力也会相应上升。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要求随叫随到的日子“不能视作闲暇时间,因为休闲的重要功能——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有限。”
(3)
反思与反抗
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法国Sophia Antipolis大学心理学家法比恩·马西发现,自己一年内在工作时用来阅读、书写和归类电子邮件的时间至少达到600小时。换算下来,相当于6、7、8三个月份每天花8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发现这件事情后,他感到十分震惊,所以决定在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构建一道屏障,他放弃了智能手机,拒绝在下班后登录工作邮件帐号。
以工作环境优越见称的法国严格遵守每周工作35小时的限制,但现今人手一机,不少人下班后或在周末仍用手机及电脑处理公务,无法好好休息。法国研究组织Eleas于2016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员工在上班时间以外仍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工作,有六成员工希望政府能立法保障他们的权益。
最终,法国决定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该法律要求雇用员工50人或以上的企业必须与员工协商制定新的“邮件准则”,确保员工休息时间。如果这样的准则无法达成,企业必须制定出员工在晚间和周末无需处理邮件的具体时段。法国劳动部部长米里亚姆·艾尔·荷姆表示:“我们需要提前预测一些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在如今这种永久联网状态下,人们要如何平衡私人生活和工作时间。”
不过,根据2015年的数据,全法国共有48.6%的企业员工在“小型”企业里工作。也就是说,即使是从法律层面来说,有将近一半的法国员工无法享受到“断网权”政策的庇护。
从2014年开始,德国职场对于现代通讯工具给日常工作造成的心理混乱开始重视起来,如大众汽车规定,员工下班以后就不能发工作邮件,大众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公司尊重员工的自由时间,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雇主才能打断员工的休闲时间。
在中国,人们也意识到随时在线的巨大负面影响。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在2019年5月在印发了《香洲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以下简称《措施》)[35],要求各单位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微信工作群,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群成员发言须有实质性内容,不得刷屏点赞和发表情包;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因专项工作组建的微信群在结束工作后应及时解散等内容。同时,《措施》还规定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开设新媒体账号,原则上一个单位在同一平台只开设一个账号;不得利用新媒体变相搞新闻报道,大幅报道本单位领导日常政务工作。![]()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一书。)

作者: 波波夫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0
页数: 336
定价: 59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20716550
[2] Jennifer Moss,Burnout Is About Your Workplace, Not Your People,HBR,December 11, 2019
[3] Freudenberger H J.Staff burnou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
[4 ]Maslach C,Schaufeli W B,&Leiter M P. et al. Job burnout.Annual Review Psychology,2001
[5] 张伟、吴珊,《工作倦怠现象正袭扰中国社会 公务员倦怠度最高》,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7日
[6] Jen Fisher ,Workplace Burnout Survey ,Deloitte US,2015
[7] 《德甲名教因“工作倦怠症”辞职》,德国之声,2011年9月22日
[8] 李小雪,《韩国婚恋调查:工作疲劳影响恋爱关系》,2016年6月29日
[9] 姚力杰,《日本四成医生染上“工作倦怠综合征”》,生命时报,2014年5月27日
[10] 郑建君,《关注: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的调查报告》,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
[11] 袁野 , 《“职业倦怠”是矫情吗》,青年参考 ,2019年9月06日
[12]《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压力全球第一 上海压力最大》,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2012年9月29日
[13] 张钟凯 刘刚,《调查显示:台湾上班族普遍压力大 低薪是主因》,新华社,2017年11月1日
[14] 张文婷,《调查显示:工作压力是企业员工健康风险首要诱因》,人民网,2015年7月13日
[15] What are the 5 stages of burnout?,thisiscalmer.com,April 10, 2019
[16] 周生生,《如何化解职场恐惧症?》,前程无忧网站,https://arts.51job.com/arts/41/303710.html
[17] 《职场人厌班情绪调查报告》,脉脉数据研究院,2017年11月
[18] Jory Mackay,How to deal with burnout: Signs, symptoms, and strategies for getting you back on track after burning out,RescueTime blog,January 29, 2020
[19] Robert Kubey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ddiction is no mere metaphor,SCIENTIFIC AMERICAN,FEBRUARY 2002
[20] Jen Fisher ,Workplace Burnout Survey ,Deloitte US,2015
[21] Generation Uphill, Economist, Jan. 21st 2016
[22] 《千禧一代的谬论与现实. ——教育、工作与社会态度》,益普索Ipsos,2017
[23] Anne Helen Petersen,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BuzzFeed, January 5, 2019
[24] Eric Fish ,China’s Millennials: The Want Genera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5
[25] Jessica Jones,Spanish millennials are reshaping their goals to afford life,BBC,28th November 2018
[26] 《2019德勤千禧一代年度调研报告》,德勤,2019
[27] Roula Khalaf,A bitcoin bubble made in millennial heaven,Financial Times,January 12, 2018
[28] American millennials think they will be rich,Economist, Apr 22nd 2019
[29] 《联想研究显示,科技对提升职场工作效率发挥重要作用》,中华网,
[30] 《调查: 七成受访者下班仍回工作电邮》,联合早报,2019年7月12日
[31] 邹倜然、程文雅、郁诗怡,《下班后,“工作微信”该不该回?》,2018年9月18日
[32] 《超长工作伤己伤家人,学会休息是关键》,生命时报,2015年8月25日
[33] 董乐,《研究:超长时间工作增加中风危险》,BBC中文网,2015年 8月 20日
[34] José Luis Peñarredonda,What happens when we work non-stop,BBC,24th August 2018
[35] 张炳剑,《微信工作群的指尖之苦,实是形式主义之累》,钱江晚报,2019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