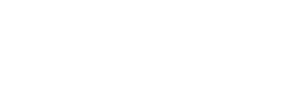No.57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在2022年初的科技向善创新周上,提出人与周遭的互动经过三个阶段:离线、在线、在场。
“离线”是一种“天然”在场,而从“离线”到“在线”,基于对效率的追求或由于技术的限制,社会活动的本源被抽象出来,省略掉很多细节。而从“在线”走向“在场”,是一个把我们之前丢弃的有价值的细节重新找寻回来的过程,最终实现线上和线下完全相同的效果。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技术之所以在当下涌现,是因为其符合从“在线”走向“在场”的趋势。
在场感构成元宇宙的突出特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线上和线下体验一致,我们尚不知晓。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在线”和“在场”,是否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
风险投资家马修·鲍尔(Matthew Ball)如此定义元宇宙:“元宇宙是一个由持续的、实时渲染的3D世界及模拟构成的广阔网络,支持身份、对象、历史、支付和权利的连续性,并可实现有效且无限的用户同步体验,每个人都具有个人的在场感。”
从本质上讲,让我们得以体验元宇宙的虚拟现实技术,是让用户沉浸在一个栩栩如生的数字世界中。你看到的东西填满了你的整个视野,并且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获得追踪。在理想状态下,这种体验唤起了我们所说的“在场感”(presence)。这带来一种亢奋,而且具有难以捉摸的属性:超越性的、被远距传输的刺激,你觉得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中身临其境,而不用考虑自身实际上不过是在原地站着或坐着,似乎可以一下子逃离眼下的世俗事务。
与今天的互联网不同,元宇宙力图给人一种到场的幻觉。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将元宇宙描述为一个具身的互联网(embodied internet),其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最核心的议题就在于,如何在空间不在场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在场。如何复制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是社交媒体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这一真实感则取决于它将用户传输到该环境中的程度,以及用户的物理行为与其化身之间边界的透明度。
当然,就个人交往而言,在场感意味着在一个虚拟空间中与虚拟的他人一起实际存在的感觉。例如,将来不再只是通过屏幕进行交流,而是“你将能够作为全息图坐在我的沙发上,或者我将能够作为全息图坐在你的沙发上……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让我们感到与人更多地在一起”(扎克伯格语)。这种身临其境感可以提高在线互动的质量。
究其根本,元宇宙实际上对我们关于感官输入、空间定义和信息获取点的假设进行了重新配置。这带来了一种感官上的飞跃,把我们从物理兴趣点、经纬度、边界以及对导航的适应等引入到更复杂的概念中,比如无意识中识别的那些“地点”、动作和存在。
即将到来的元宇宙是由软件和硬件共同促成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对作为空间的共享幻象的信念。与网页和APP相比,元宇宙与立体感知、平衡和方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通过电脑和手机与元宇宙互动,但同VR的沉浸感和通过AR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数字持久性相比,这种互动是简陋而粗糙的;但反过来说,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也不尽如人意,笨重的头盔只能提供孤立的体验,玩家很少有机会与拥有设备的其他人进行交叉游戏。人们期待,元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网络空间,能够将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化身可以从一个活动无缝跳转到另一个活动。
扎克伯格曾对投资者表示:“元宇宙的决定性品质是在场感,也就是你真的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或在另一个地方的感觉。创造、化身和数字对象将成为我们表达自己的核心,这将带来全新的体验和经济机会。”
如果把元宇宙作为一个持续的全面经济系统,将会有无数的化身和数字资产与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和经济体进行互动,当现实个体与公司机构都在元宇宙中拥有自己的经营空间并随时参与其中进行活动时,数字持久性和数字同步性就成为元宇宙必不可少的“自我要求”,这意味着元宇宙中的所有动作和事件都是实时发生的,并具有持久的影响。
实时性可以被认为是在场感的另一面,也是此前互联网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它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一是通信技术可以支持代理人同时执行动作;二是动作的及时性需要内嵌在平台设置中。
在模拟环境中,代理可以是一个人、很多人或者非人,另外,用户可以由许多被称作化身的实体所代表,也可以被许多软件代理所代表;于是在这样充斥着大量代理和化身的元宇宙系统中,就要保证所有动作、反应、交互都必须发生在实时共享的、具有时空连续性的虚拟环境之中。这要依靠充分提高计算机的计算效率、增强计算机的算力才能实现,这也正是Web 1.0和Web 2.0无法真正实现实时性的技术局限所在。
代理和化身直接牵涉到身体问题。扎克伯格在推广Meta的元宇宙愿景演讲中使用了自己的卡通化身,但他最终希望元宇宙包括栩栩如生的化身,其特征将更加逼真,并从事许多与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所做的相同的活动。
“我们的目标是既要有逼真的化身,又要有风格化的化身,创造出与人同在的深刻感觉”,扎克伯格在品牌重塑会上说。
如果化身真的在路上,那么我们将需要面对一些关于我们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棘手问题。这些虚拟版本的自己,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身体的感觉,是好还是坏?可以预期,一些人将对看到如同自己一样的化身感到兴奋,其他人则可能担心这将使身体形象问题更加恶化。如果社交媒体构成前车之鉴,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元宇宙中的虚拟化身,会对人们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的感受和生活产生影响。
伴随着20世纪后半叶新技术革命的启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都发生了“身体转向”。“身体”愈发受到关注,且近年来这份关注有增无减。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数字媒介,正在构建一种去“身体”的文化,从计算机到智能手机,再到穿戴式设备和虚拟现实头盔,这些数字革命催生的新媒介无一例外都在用“远程在场”代替“肉身在场”,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把身体径直放在争论的中心, 这不是时尚, 而是当务之急——因为科学家、工程师正在对它进行重构和重组。”
在元宇宙中,身体成为了“化身”,存在也成为了“电子存在”,数据和信息的有效集成构成“我”在元宇宙中的真正意涵。身体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型媒介,同时也是历史的、文化的、技术的,正如安德烈·莱罗-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认为,人类的进化包含两部平行的历史:有机史(进化史)和无机史(技术史),二者并非是平行的而是汇集于一体的。身体和思想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文化属性,这一点不仅有现象学的分析,还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背书,比如人类的消化道特征决定了人需要过一种集体性的生活。而当“远程在场”将身体抛出在外之后,丢失的不仅是非语言沟通中不可被语言复制的符号讯息,还有身体本身所携带的巨大的文化和道德意涵。
社交媒体自创生伊始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身体缺席的技术前提下实现沟通的在场。正如比尔·盖茨在1999年曾说:“如果我们要复制出面对面沟通,那么我们最需要复制的是什么?我们要开发出一个软件让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开会——该软件能让参与者进行交互,并令他们感觉良好,在未来更愿意选择远程在场。”
然而,假如元宇宙在模拟了身体的感觉经验的同时,肉身依然是被排除在互动关系之外,那么,元宇宙空间的社会契约就会减弱它的约束力(正如我们今天在网络空间中看到的混乱和戾气一样),一个以遇见他者为目的的虚拟社区,会因为身体及其背后文化结构的不可见,而难以真正实现一种“面向他者的传播”。
在元宇宙中,身体其实永远是一项需要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化身技术必须走一条精细的路线,既要保持足够的真实性,以忠实于人们的身份,又不能威胁到化身背后的人的心理健康。
现代社会是基于视觉媒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自然化”存在、常态化运作以及合法性来源都是“书写”。19世纪以来,几乎每一种“新媒介”都是对书写的致敬:摄影是用光“书写”,留声机是用声音“书写”,即使是今日不断发展出新技术且创造出无数个新名词的互联网新媒体,也是用代码“书写”。书写完成了一次空间与时间的置换——用空间置换时间,因为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是人类唯一能型塑的对象,于是当书写媒介中介化了现代社会之前的面对面传播,“在场”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各种视听媒介中介化了的“幻象”。自有信息革命,如何在被各种媒介中介化了的传播中模拟出在场感,即成为了数字技术的兴趣和使命。
曾几何时,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媒介技术的演进改变了这一点。共享的体验原本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信息,作为媒介的主要产出,却把生活体验变成了无止无休的新闻标题。通过信息消费而获取的关于事件和人物的知识压倒了有关体验的叙述。信息创造了一个事件丰盛但体验匮乏的世界。体验逐渐在我们身外发生,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奇观(spectacle),而我们则成了这种奇观的观众(spectator)。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件的传播丧失了叙述的权威。
现在,一个人可以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成为某种社会表演的观众。这种表演的舞台找不到具体的地点标记,其结果是,一度把社会分成许多独特交往环境的物理结构的社会意义日渐降低。传播技术允许公民同身体上缺场的行为主体和社会过程建立某种程度的连接,通过这种连接,他们的体验和行为选择被重新结构化。
历史上,对于前现代的人来说,缺场的权力之源——例如君主和教会的扩大化的统治——注定是不可见的和不可渗透的。随着传播技术的扩散,情况变得极为不同。这些技术强化了在地方生活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侵入之间建立“工作联系”的潜力,与此同时,经由象征的撒播创造了新的远距离关系:“亲身体验”和“中介的体验”日益交织在一起。
这一切所指向的是,场所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在场”与“缺场”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场所总是一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场所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在当下的互联网上,以及未来的元宇宙中,线上一个ID、一种影像化的存在即可以表示我们在场,但在这些符号的背后,屏幕那端的个体究竟是谁,其以何种状态与我互动都是未知的。这在在线教育模式中充分显露,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在线学习资源,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沉浸式课堂,还可以自行制作自己的多媒体作品或者进入学习社区获得机器学习的反馈,但基于现实的连接始终缺位,学生缺乏同伴的在场陪伴,师生无法在互动中确认彼此信息的接收度,也缺乏面对面的真切体验。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不同步在线也可接收信息的便利之时,也带来了空间感与意义感的消失。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通过现实空间与身体在场感传递的意义远非数字化可以模拟,学校、电影院、教堂等场所的存在,正是为了诠释了身体在场对于互动仪式和情感意义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化生存”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我们从一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世界,第一次来到了一个“海内存知己,比邻若天涯”的世界。从今而后,由于虚拟世界的打扰,我们永远在场,而又永远缺场,用句时髦的话来说,我们永远生活在别处。
对于司晓所说的从“在线”到“在场”,我们也可以作不同的观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扎克伯格或者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坚定不移的元宇宙热情。AR游戏Pokémon Go背后的开发商Niantic创始人兼CEO约翰·汉克(John Hanke)就把元宇宙比作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他写道,那些激发了元宇宙概念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实际上“是对技术出错的乌托邦的未来警告”。
扎克伯格认为,虚拟世界会为你生活中的人和你想去的地方带来更强的在场感,而汉克却相信,它将起到相反的作用。他在博客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向增强现实的‘现实’靠拢——鼓励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站起身来,走到外面,与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联系。这是我们人类生来要做的事情,是200万年人类进化的结果,因此,这些是让我们最快乐的事情。技术应该被用来使这些核心的人类体验变得更好,而不是取代它们。”
严格来说,有关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价值之间的争论,不太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在未来,那些认为物理世界更重要的人将会说其他人在虚拟世界中出现了问题,反之亦然。
研究在线连接心理学超过三十年的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过去的数年里,一直呼吁“重拾交谈”。本来全力关注虚拟空间的她,着迷于一个新的问题:在一个许多人说他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交谈的世界里,面对面交谈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研究了家庭、友谊和爱情。她研究过中学、大学和工作场所。她震惊于如果人们停止面对面交谈,或者是在有电子设备的情况下不能够专注于交谈,那么人类的一种最宝贵的品质——同理心就会下降。
我们已经习惯了无时无刻的连接,但代价是我们绕过了交谈。五年前应邀为特克尔的《重拾交谈》一书写推荐语,我写道:“现在迫切需要重拾这样的认识:雄辩是廉价的,而交谈却是无价之宝。”至少在开放式和自发性的交谈中,我们允许自己完全在场和显示脆弱。我们学会了眼神接触,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姿势和语气,互相安慰,有理有节地挑战对方。由于这一切,同理心和亲密关系才得以蓬勃发展。在这些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自己是谁,并学会自我反思。
感同身受的交谈能力与独处的能力相辅相成。在独处中,我们找到自己;我们为自己准备好交谈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真实的,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聚拢自己,就无法认出其他人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忍受孤独,就会把别人变成我们需要的人。假如人类不懂得独处,将只知道如何孤独。虽然我并不想将在线、在场与交谈、独处进行过度对立,但沿着特克尔的思路,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不间断的联系,幻想中的在场,是否会让人类陷入更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