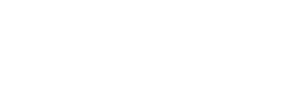鲁迅往事: 从横滨到仙台的日子

鲁迅于1902年4月4日抵达横滨,4月下旬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就读。1900年以后,赴日的中国留学生迅速增加,1902年约有500人,数量最多的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和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约有8000人(另一说法是13000人)。弘文学院,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为“清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位于当时的牛込区五轩町,其后为了避开乾隆帝的名讳弘历,改名为“宏文学院”。学校课程分为普通科和速成科。普通科是为升入各地的高等专门学校或大学而设的预备教育课程,学制二至三年,学习日语和一般的基础科目。速成科是一种依靠翻译人员学习师范、警察事务、物理化学、音乐等专业科目的短期培训课程。鲁迅在这里上了两年的普通科,与六人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直到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
当时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继续积极开展启蒙活动,其独特明快且自评为“笔锋常带情感”的文体令青年们倾倒不已。继《天演论》之后,严复在上海又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1901—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1903)。鲁迅也是这二人的忠实读者。

另一方面,以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为契机,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义和团事件,是指甲午战争后中国北方民众直接起义,反抗列强入侵的一次武装斗争。义和团势力壮大之后,清政府主动向列强宣战,然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等人却率领少数高官逃往西安,反过来颁布了讨伐义和团的命令,任由北京被八国联军侵占。慈禧太后等人与列强媾和后回到北京,采取“新政”,鲁迅等人赴日本留学就是凭借这一“新政”。此次事件令列强认识到通过“瓜分”政策进行直接统治的弊端,索性转向利用清朝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保全”政策。变法派原本的设想是通过引入立宪制度,在保存清王朝体制的同时达成现代化,然而清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让人们对变法派的观点产生怀疑,由此形成了否定清政府乃至清王朝体制本身的“革命派”。
这一年,早前曾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孙文(号中山)在广东省惠州市发动起义,但遭到失败。经过义和团事件之后,曾参加过变法运动的章炳麟转向了“排满革命”的主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市民们主动当起了“顺民”,没有一名汉人官员愿意为清政府牺牲的事实改变了他的想法。章炳麟开始认识到,倘若不“驱逐”满人,就不可能唤起读书人的爱国心和民众同仇敌忾的意志,长此以往汉人将会变成欧美列强之奴(清政府)的奴隶。1902年,章炳麟赴日与孙文会谈,打算4月26日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却遭到日本警察的拦阻。
然而,“排满”革命的思想从此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深入人心。鲁迅进入弘文学院就读,正是在此时。翌年,章炳麟在上海出版的《苏报》上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并亲笔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判变法派并提倡革命。邹容和章炳麟因此被捕,邹容身死狱中,章炳麟度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二人都主张中国和波兰、印度一样已经“亡国”,已经成为他国的“奴隶”,批判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邹容借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宣扬天赋人权和民主主义,对侵蚀国人的奴隶精神提出尖锐批判,他指出“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接着呼吁“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邹容死在狱中时年仅二十岁,当时《革命军》的销量已超过百万册。鲁迅后来写道:“倘说[对革命的]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杂忆》,1925)当然,留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在速成科轻轻松松地学习新知识,归国后在“新政”之下求得一份利益丰厚的工作。由此可见,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说是一个新旧思想的大熔炉。
在弘文学院学习之余,鲁迅也会去“清国留学生会馆”、逛书店、参加集会、听讲演。无论是邹容,还是后来领导革命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当年都曾经在弘文学院就读。鲁迅入学半年后,来自杭州求是学院的同乡许寿裳也来到了弘文书院。此后,许寿裳成为鲁迅的终生挚友,始终支持着他。据说两人经常一碰面就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欠缺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们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诚”与“爱”,而最大的病根是曾两度被异民族奴役。二人的结论是奴隶怎么可能会谈论诚与爱呢,救赎的方法唯有革命。后来,“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思想轨迹中最大的支柱性论题。不过这绝不仅仅只是革命派的论题。毋宁说,这反倒是写出《中国积弱溯源论》(1898)、《新民说》(1903)等文章的梁启超等人更热衷探讨的问题。不过,鲁、许二人在考察国民性的缺陷时,着眼于汉民族被统治的奴役状态,认为有必要通过“革命”从这种状态中实现自我救赎,这表明他们的思想与章炳麟、邹容已十分相近。
1903 年 3 月,鲁迅在留学一年后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辫子是清王朝在统治全中国时将其民族习俗强行推广的产物。“剃发令”(辫子令)颁布时,尽管各地汉人曾发起过反抗,迎来的却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在清朝近 300 年的统治中,包含这一历史的辫子已成为汉族人的习惯,它的由来也遭到遗忘。然而随着人们对清朝政治体制心生怀疑,辫子开始被视为一种耻辱的象征,它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是异族奴隶的事实。不过,剪辫子并非一件易事。日本曾出现过的一种侮辱性称呼—“辫子佬”,就是指留这种辫子的人,所以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速成科的学生会采取一些应对的临时手段,或是将辫子盘起藏在帽子下面,看起来像是高耸的富士山,或是把辫子解开后用油梳平再盘起来。剪辫子的困难重重,即便是鲁迅本人,在这一年夏天回乡时也不得不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
当时许多来自中国各省的留学生纷纷组织了本省的同乡会,并出版杂志。浙江省的百余名留学生组成了“浙江同乡会”,将会刊命名为《浙江潮》。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该杂志的编辑。受其邀请,鲁迅 1903 年 6 月在杂志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讲述波希战争中,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的军队在温泉关峡谷布阵迎击波斯人的军队,但寡不敌众,最终除国王外悉数壮烈牺牲的故事。在此之际,唯有阿里斯托德摩斯一人因眼疾脱离前线,并偷偷在深夜回来找妻子赛琳娜,然而赛琳娜严厉地斥责丈夫,说他违背了斯巴达战士“不胜则亡”的精神,随后自戕而死。在翌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摄政王波桑尼阿斯指挥下的斯巴达军队终于在与波斯军队的血战中一雪前耻。战场堆积如山的尸骨中出现了阿里斯托德摩斯的尸体,是他悄然赶来并战死疆场。
1903 年 4 月,趁义和团事件出兵的俄国军队久驻中国东北不去,并要求签订条约,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以留日学生为中心的中国人民发起了“拒俄运动”,鲁迅的这篇文章便写于运动的高潮。学生们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同时给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去电报,要求其北上抗战,由此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爱国学生运动。对此,清政府却以“借‘拒俄’之名图谋革命”的罪名对运动大肆镇压,许多知识分子从此抛弃对清王朝的幻想,转向革命派。无论是黄兴、陈天华等以湖南、湖北两省为中心成立的“华兴会”,还是蔡元培、章炳麟等以浙江、江苏两省为中心组建的“光复会”,都是在拒俄义勇军改组后的“军国民教育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斯巴达之魂》试图唤起当时被频繁倡导的“尚武精神”。尽管这篇少作“激昂慷慨”的稚嫩文风令鲁迅多年后颇感羞愧,但文章以一名叛逃者摆脱耻辱的过程为故事中心,讲述斯巴达军队决心以死雪耻的战斗,已然展现出鲁迅文学的重要一面。
同年,鲁迅翻译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1]鲁迅的这两部译作,与其说是分别重译自井上勤翻译的《九十七时二十分月界旅行》和三木爱华、高须墨浦翻译的《拍案惊奇地底旅行》,倒不如说是对上述译本的改编。较之以满腔激情的文言文写作的《斯巴达之魂》,这两部译作采用白话文,沿袭了章回体小说的风格。两部译作试图根据当时梁启超提倡的启蒙小说理论,借白话小说的力量普及科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巴比康等人打破引力束缚,成功飞向月球,以及黎登布洛克跨越自然界诸多障碍,持续地底探险的行动,均被定义为严复《天演论》中“天”与“人”的斗争,即人作为天的奴隶,凭借自身意志、想象力和工具的力量,一步步摆脱天的支配这一漫长进化过程的当下表现。
此外,鲁迅还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说鈤》(1903)和《中国地质略论》(同年)。前者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的情况;后者则论述了正被列强逐步侵占的中国煤田的形成与分布状况。在中国留学生群体混杂动荡的思想熔炉中,我们可以看到拥有科学与文学两种可能性的青年鲁迅在尝试、摸索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尽管清政府指定的升学方向是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冶金系,但他却选择了医学。鲁迅当时的梦想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他对医学的热情,甚至让一位原定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朋友回心转意,改学医学专业。鲁迅非常反感那些为了拿文凭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会让帽子像富士山一样高耸,会在留学生会馆里兴高采烈地跳舞,会成群结队去上野赏花。所以他决定远离喧嚣的东京,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时鲁迅在心里,想必强烈地渴望暂时远离,以潜心学医。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1904 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仙台医专是1902 年第二高等学校医学部独立后成立的学校,也是后来的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今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东北大学的片平丁校区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几栋建筑。
面对首位中国留学生,仙台医专不仅免试、免学费录取,还派学校职工帮忙寻找住处。鲁迅最初的住处是在广濑川沿岸片平丁五二番地的佐藤屋,与青叶城趾隔岸相望;大约两个月后又搬到此处往南约 300 米的土樋一五八番地的宫川宅。两处都在位于片平丁的学校附近。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因《朝花夕拾》中收录的《藤野先生》(1926)一文而广为人知。此外,1978 年日本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仙台鲁迅记录研究会编,平凡社),通过当时的报纸、记录、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详细说明了鲁迅的勤奋求学,以及当时仙台和仙台医专的状况。
在此,我们可以通过近年发现的一封鲁迅致友人的书信(《致蒋抑卮》,1904 年 10 月),来看看鲁迅到仙台一个月后的生活。
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厪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
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任克任送来两本书,其中《释人》为清朝孙星衍所著,是一篇关于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或许是出于对医学生鲁迅的好感,特地送来了手抄本。而《黑奴吁天录》则是林纾翻译的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 1901 年于杭州出版的魏易家刻本。林纾在清朝末年翻译了大量欧美小说,他的翻译被称为“林译小说”,译作数量超过 170 种。林纾本人不通外语,他的翻译方法是先由魏易等协助者口述作品内容,再由他译成文言文,不过林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最早让中国了解欧美的文学世界。鲁迅爱读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茶花女》)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司各特《艾凡赫》)。其中,描绘美国黑人奴隶悲惨境遇的《黑奴吁天录》,极大地唤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
在始于 1904 年 2 月的日俄战争中,日军虽然死伤惨重,但仍接连胜利,仙台市民和学生频频列队庆贺。在仙台的鲁迅远离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鲁迅称他们是肩负中国未来的主人翁),由于生活在日本人的社会之中,因此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学校里,他都能细致地观察到日本人对战争进展时喜时忧的状态。在他的同学中也有一些较年长的上了战场。旅顺陷落后,曾有 1500 余名俄国战俘被押送至仙台。日俄战争是日本正式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积极地统治殖民地,并卷入列强间冲突的转折点。鲁迅信中的“阿利安人”,是指日本人,他们虽是黄种人却沉浸在类似白种人的优越感之中。
同学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神色暗淡、安静认真的学生。学校的便门前有一个面向学生的乳品店。据说只要来这儿,就总能看到先到一步的鲁迅一脸笑眯眯的样子,因为在这里可以自由阅读报纸和政府公报。

从鲁迅的信中,既可以看出每日学习对他而言相当辛苦,也能看出他不满于全是死记硬背的学习。而且鲁迅在信的末尾还做了补充,告知对方自己中断了此前一直在翻译的《物理新诠》,表示“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可见鲁迅即便压抑自身的其他可能性也要一心学医的态度。
信中还说“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鲁迅在此遇到了一位终生难忘的老师。第一学年的主要课程是德语(每周八小时)和解剖学(每周八至九小时)。解剖学有两位授课老师,其中一位是藤野严九郎教授。据当时的学生描述,藤野先生“人如其名,严格无比,以给分低著称”“上课严肃至极,人人惧怕”。他着装不修边幅,时常忘了系领带。传闻有一年冬天,他穿了一件非常破旧的外套,因此被电车司机误认为是扒手,司机甚至提醒其他乘客多加小心。开课一周后,藤野先生将鲁迅叫到研究室,问他是否能做好笔记,让他把笔记本拿给自己看看。笔记本提交二三日后便返还了,令鲁迅惊讶不已的是藤野先生在笔记本上用红笔细心地添改,不但补上了遗漏的地方,甚至连文法错误都一一订正了。如此一直持续到授课结束。
每年春、夏、冬季的假期,鲁迅都会离开仙台的日本社会,放下勤学的生活,到东京与许寿裳等人碰面。1904 年 11 月,以浙江人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12 月陶成章等人来到日本,以留日浙江人的秘密组织“浙学会”为主体,建立光复会东京支部。身为浙学会会员的鲁迅和许寿裳也加入其中。在一次往返途中,鲁迅在水户吊唁了明朝遗民朱舜水的遗迹。
1905 年 6 月,学年期末考试结束后,一到暑假,鲁迅便了去东京。8 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项纲领,孙文任总理,黄兴任副总理。同盟会的总部设在东京,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国、美国、加拿大等地设立支部。不过,光复会成员全部 加入同盟会,并不意味着光复会就此解散。鲁迅作为光复会[2]成员,并未加入同盟会。同样是在这一年,清政府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历史正一步步发生重大转折。
鲁迅 9 月回到仙台时,学年考试的成绩已公布。鲁迅的成绩是六门课程平均分为 65.5(丙等),在 142 名学生中排第 68 名,各科成绩分别是伦理学乙等,组织学、生理学、化学、德语丙等,解剖学丁等。当时的成绩评定相当严格,查看保存至今的成绩册可知,在所有学生的成绩中丙等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果一名学生有三门以上课程的成绩为丁等就会留级,当时有 30 名学生留级。于是,只有一门是丁等的鲁迅可以升入二年级。然而,有传言称鲁迅之所以会合格,是因为藤野先生在他的笔记本上做了记号,透露了出题范围。虽然《藤野先生》一文中的记述与当时同学的记忆之间多少有些差异,但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根据鲁迅作品的描述,他将此事告诉了藤野先生,一些同情鲁迅的学生和他一起谴责学生会干事无端检查笔记本的无礼行为,要求公布调查结果,传言才得以平息。此事又被称为“试题泄露事件”。实际上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表示不合格的丁等,因此这个传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谎话。或许正如鲁迅的同学所回忆的,那是留级生们半是嫉妒半是恶作剧的产物,以此对评分严格的藤野先生表示反感。但此事却让鲁迅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对他而言,这并非是单纯的诬陷。他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 60 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藤野先生》)这绝非鲁迅基于受害者角度的臆想。因为在支配与被支配、歧视与被歧视的关系之中,支配者、歧视者往往难以看到或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存在。不容否认的是,日本学生恶作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到了第二学年,藤野先生负责教授解剖学实习(每周十小时)和局部解剖学(每周二小时)。藤野先生想知道中国女性是如何缠足的,足骨会变成怎样的畸形,一度让鲁迅非常为难,不过在人体解剖课上,仅鲁迅参与解剖的尸体就有 20 多具,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据说大约是在 1905 年的寒假,来到东京的鲁迅向许寿裳讲述了胎儿是如何被巧妙地保护在母体之内、矿工的肺部是如何被粉尘污染变黑、父母的性病是如何给孩子带来残酷伤害的。此时,光复会的徐锡麟来到日本,鲁迅到横滨迎接与其同行的马宗汉、陈伯平、范爱农等人。此事在《朝花夕拾》的《范爱农》(1926)一文中可见。同行者中还有王金发。这或许也是鲁迅身为光复会成员的工作吧。11 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立刻在留学生中引发大规模抗议行动。围绕抗议行动的形式,留学生们分成了主张全体即刻回国的归国派和继续留日派,两派之间爆发激烈论争。秋瑾(出身绍兴的女性革命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批判包括许寿裳、鲁迅在内的继续留日派。论战正酣之时,《朝日新闻》刊载报道称“此乃清国学生过于偏狭解释文部省命令而心生之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致,其团结亦甚为薄弱……”,于是发生了陈天华为表抗议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的事件。
陈天华的抗议并非是愤慨于“放纵卑劣”这一无端诽谤的评语,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3]
换言之,他在抗议诽谤者的同时,试图唤起那些招致诽谤之人的自省与耻辱心。最终,秋瑾等 200 多人回国,余下的主张稳健的继续留日派占据上风,向文部省的命令妥协。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一度有 8000 名留学生参与的重大事件。
过了元旦,1906 年寒假过后进入第二学期,鲁迅的课程新增加了一门细菌学。课堂上常用幻灯片展示细菌的形态。授课提早结束时,偶尔会放一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由于当时日本刚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所以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鲁迅因此看到一个被日军俘虏的中国人双手反绑、将要被砍头的画面。被处死的男人四周围着的,同样也是中国人。根据解说,正要被斩首的是一名“俄探”,也就是为俄国军队做间谍的中国人,而围在他四周的都是看热闹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健壮的体格,而神情是一样的麻木。在遥远的仙台,站在日本同学之中的鲁迅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情景。这件事又被称为“幻灯片事件”,而此时冲击鲁迅的情绪与“试题泄露事件”时并不相同。这是同胞被确确实实杀害的屈辱性情景。然而,鲁迅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屈辱和愤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被残杀的同胞周围,鲁迅不得不看到其他同胞们麻木不仁的神情,他们似乎并没有对被杀者的屈辱感同身受,这表明他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感情。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作为施害者的日本人毫不愤怒。但对他而言,同胞们招致屈辱的状态才是他不得不追问的对象。此时笼罩在鲁迅心头的,恐怕是一种始终伴随着愤怒和屈辱的深沉悲愤,以及作为人的羞耻感。在之后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反复观察到同样的结构和意识。鲁迅之所以选择在《〈呐喊〉自序》中用“幻灯片事件”来说明自己弃医从文的转变,是因为这正是他文学根源的原初场景。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鲁迅当时的观点是,必须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换言之,对于被强加的屈辱,中国人必须重拾敏锐的感觉以及对彼此的同情心,中国人必须成为人,而不是被压迫、被割裂的奴隶。
鲁迅没有参加第二学期的考试便离开了仙台。看到藤野先生与自己告别时的悲哀神情,鲁迅只好撒谎说自己要去研究生物学,从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还是会派上用场。藤野先生叹息说,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在生物学上并没有用武之地。临别时,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惜别”。这张照片后来被挂在鲁迅北京寓所的书房墙上。《藤野先生》写于 1926 年,鲁迅在文中这样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1934 年,增田涉就《鲁迅选集》(增田涉与佐藤春夫合译,岩波文库)的收录作品一事征求鲁迅意见时,鲁迅表示唯有《藤野先生》一文一定要收录其中。鲁迅期待着借此得知先生的消息。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另一半落了空。以《鲁迅选集》为契机,人们得知藤野先生依然健在,并在家乡福井县本庄村的一家诊所为村民治病,但此时鲁迅刚过世不久。
(本文节选自《明暗之间:鲁迅传》)

译者:陈青庆
定价:69元
出版日期:2021年9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光启书局
[1] 《月界旅行》原名 Dela Terre à la Lune,现通译《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原名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现通译《地心游记》。——编注
[2] 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有不少会员加入,但有部分人并未加入,坚持独立
[3] 此段日文省略了中文绝命书的部分内容。中文绝命书完整段落为“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