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走的人关灯,人类的任务是迎接智能机器的来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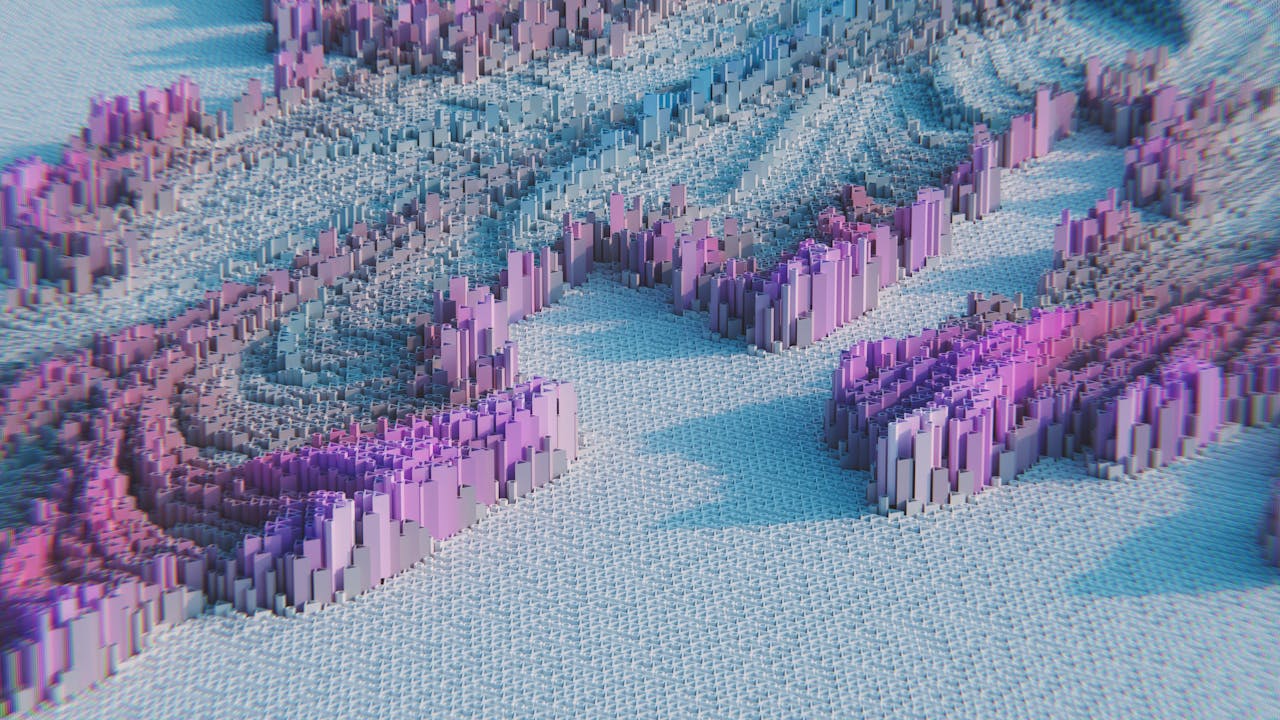
1957年,休·艾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III)在普林斯顿进行他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时对量子力学进行了阐述,但他的观点却被忽视了,很快他就离开了学术界。然而这个诠释从学术上讲比其他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消除了由量子力学所揭示的荒谬事实形成的谜团。
在传统的解释中,一个粒子的几种可能的态在波包中叠加,波包以随意的方式缩小,这将有利于其中一种态,而淘汰其他的态。在艾弗雷特被称为“多世界诠释”的阐述中,每一种态的最初叠加都可实现,但由于他们是不兼容的,一个这样的物质化过程只能在不同的物理宇宙中实现:最初叠加的分解是在平行的宇宙中通过裂殖生殖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就像持续不断喷射的烟花,不断更新。从任何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开始,历史都是以树状结构发展的。
用物理学家迈克尔·普莱斯(Michael Price)的话说:
“根据多重世界的假设,一个量子相互作用的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实现。在观测时波函数并没有减少,而是以决定论的方式继续发展,覆盖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这些结果都同时存在,但他们之间却不互相干扰。他们分散在许多完全真实的世界中,但彼此却不能相互看到。这些世界构成一个整体。”(普莱斯,1994—1995)。
在《为什么我们像猫一样有九条命》(2000)这篇文章中,以这个诠释所得出的结论为基础对一个活着的人在持续分裂的世界里的状态进行了一些尝试。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偶然发现一个态的叠加,其中一个意味着我们已经死亡,而另一个意味着我们还活着。我们完全忽略了正在发生的现象。我们对自己的意识一定是存在于我们还活着的那个世界中。在我们死去的那个世界里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就立即消失了。
出于对这个逻辑必然性的关注,我只想重新检验一下由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设计的著名的心理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猫处于生与死的叠加态。当猫活着的时候由它的意识可以得出结论:猫处于活着的态时,猫能感觉到它活着;而当猫处于死去的态时,它永远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了。我在2000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写道:
“在上世纪30年代埃尔温·薛定谔设计的心理实验中,一只猫的生或死取决于打碎的一小瓶氰化物,而这是由量子的变异(波列的减少)所决定的。这种量子变异的产生机率是二分之一。猫同一时间在两个宇宙中分别处于生存和死亡两种状态,但这两个宇宙之间是相互岔开的。因此,这只猫既是活着的又是死了的,但是在两个相互分开的宇宙中。”
任何一个经历过在两个叠加世界中同时生存和死亡的主体都是对此无动于衷的,没有任何的知觉。它的意识只与其中一个世界相连接:也就是它所活在的那个世界里。当然,除非由某些濒临死亡状态而脱险的人叙述的经历是对物理世界真实分裂的一种体验描述。我记得这些人确认他们体验到了意识飞离他们正在生死间挣扎的躯体的感觉。当他们苏醒过来的时候,这种默想被突然打断。也就是说,在那一刻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识又被重新放回到躯体内。
任何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物体在它处于活态的那个世界里都能主观地感觉到它自身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给我的文章命题为《为什么我们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我们的知觉意识在一生过程中可以积累一些近乎奇迹的生存经验,只要我们的身体能够成功地抵抗由衰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坏。我写道:
“只要还有一个世界我可以存在其中,我的意识就会继续留在那里。这样我就总能存在于多个世界中对我来说最好的那一个。在这个世界中我依然活着。”
赞成休·艾弗雷特三世的量子力学理论会使我的一些观点有所改变吗?实际上,不会。因为,即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对他来说最好的世界里,对于每个单独的世界来说都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意义。相反,所有宇宙组成的一个总体才能形成一个整体意义。要知道,从每一个时间点T开始,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实现,但是每一种可能性只能以它单独的特有路径来实现。
无论是哪个宇宙,如果人类都像不负责任的殖民者那样无法控制地对其环境进行掠夺,那结果都是一样的:人类会灭绝。无论是赞成这个观点还是那个量子力学的理论,都不会使情况有任何改变!
如果休·艾弗雷特三世为我们提供的量子力学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我所提供的关于我们主观生活在生或死状态的相互不交叉的不同世界中的解释也是正确的;那实际上我们已经生活在那个对我们个人来说最好的世界里。这真是妙极了!就像在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1990年的电影《全面回忆》(Total Recall)中,“全面回忆”公司使它的客户们想过上一种时刻惊险的生活成为可能。但客户们却无法知道“全面回忆”公司是否欺骗了他们,也无法猜到能将他们瞬间卷走的狂风正是他们所购买的产品。
我们应该知道大自然将不会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们。大自然才不在乎我们呢,不要等着它赶来拯救我们:它经历过其他物种的灭绝,并对此漠不关心。
大自然不会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在他的冷漠中,它会淘汰掉一切行不通的;稍后它会重新开始,因为它在地球上的繁茂是一个已知数。古生物史向我们揭示了:一旦大自然以新的方式创造生命的尝试失败了,它并不坚持;很简单它会在几百万年后重新开始尝试。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完全由它掌握。
当一些基本粒子相互吸引,突然聚集在一起;并且没有任何让它停下来的因素;大自然随时准备好踏上新的探险旅程。正如黑格尔所说:大自然可能在一些战役中打败仗,有些甚至是重要的战役;但它不会输掉整个战争,因为它就是“存在”。而我们为了辨识自己才将“存在”区分为时间和空间。
如果有一天我们消失了,大自然还会再一次创造我们吗?不会了。因为大灭绝之后是新的开始,一切都会孕育出新的萌芽。由此可能产生的组合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
生命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它会给自己确定一些目标并且通常能够达到。生命活动不一定会建立进化的终极形态。未来发展的道路还没有指明。
物种的持续存在是以构成这个物种个体的不断损失为代价的:我们是不会永生的。赫拉克利特(héraclitéen)河流的汹涌波涛一路奔流却没有特别的目标。它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不要轻信“受造物”这个词:它不意味着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造物主”。相反的,古生物进化学研究清晰地表明:没有任何智能设计来支配生命活动,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极其复杂的结构,但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来自于预先进行的设计。
我在《危机》这本书中写道:
“在人类出现之前,大自然还不能利用类比。它只是靠探索伸向不同岔路的通道来发展,但这些岔路是不可逆转的、相互独立的,彼此之间不能相互作用。在每种情况下,从最简单的形式到最复杂的表现;即使再次遇到与某问题相趋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已在某处被发现;大自然都必须完全重新寻求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头足类软体动物章鱼的眼睛与高级进化的哺乳动物的眼睛很接近,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相互摹仿和借用的关系:形成这两种生物的系统发育是永远不会交汇的。”(若里翁,2008:321)
在陨石或凶猛的火山喷发而造成生物物种的大规模损毁后,大自然从零开始重新上路:它不会再使用以前用过的方法。章鱼的眼睛是很古老的,但相比于晚它2亿年的另外一个生物分支——哺乳类动物人类的眼睛设计更精妙。我们人类的视网膜毛细血管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我们对所捕捉到的图像进行再次成像时要忽略掉这些毛细血管的存在。哺乳类动物的神经分支处于视网膜前方使视神经必须出现在视网膜表面,这会导致一个不适当的盲点的产生。而章鱼的视网膜毛细血管则通过视神经存在于眼睛图像捕捉器的后面,对视野没有丝毫的影响。
由于在宇宙结构不同层面中新兴机制的出现,不能从纯物理过程中先验地推断出化学过程,也不能从化学过程中先验地推断出生物过程,这也是由于新兴机制侵入的原因。
有一些文化,特别是我们的文化,想象出造物主。造物主成了我们出现在地球上的首要原因。我们是一个或几个造物主的受造物。造物主就在我们周围。它们的存在是无法证实。但是没什么能阻止我们认为也许某天大自然能够产生与我们想象中更接近的神。
智能设计在大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但它却是人类文化所特有的。智能设计形成了生物过程之后的又一个步骤,在时间上紧随其后:
“人类(在物理、化学、生物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第四个层次:智能设计。它不存在于大自然中。智能设计能更好地利用类比。人类智慧的特点正是它运用类比的能力,它是能从完全不相关的现象中识别出类似形式的才能,尽管这种识别通常需要在极其抽象的情况下进行。”(出处同上)
然而大自然的再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只在软体动物眼睛的形成中,我们就能列出七到十条不同的进化路线)。
“相反的,人类使原本互不相关的发明创造可以互相借鉴;一个产品是许多构思、想法的综合产物,人类会重新利用一个产品中好的点子。比如,在单簧管基础上萨克斯的发明:发明家们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进行自己的研究,但为了他们日后的改进,他们从不迟疑借用由他们的对手发现的一些解决方法。萨克斯的最终形成是各种不同方法的汇集和融合。如果说人类超越了大自然的话,是因为他是唯一能进行智能设计的。如今,人类既是造物主也是受造物,但他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而不是像超自然力量那样存在于大自然之外。据我们现在所知:人类是唯一具有智能设计这个能力的。在其它的地方或是在物理学家和我们讲到的平行宇宙里也许有其它的生物拥有这个能力,但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我说‘人类’的时候,我指的当然是所有那些能够超越它们所在的大自然的物种。”
随着人类而出现的智能设计是复杂化进程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被我们称作“上帝”或者是“造物主”的神秘人物也许在将来会出现,虽然也没有什么能见证他们以前存在过。在十万年或许一百万年以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前方遥远的地平线。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上帝是我们自身的投影,他是变幻莫测的,因此以人类目前的水平还不足以了解他。
人类这个物种的出现是无法被预言的,人类文明使自然进程的延伸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物理化学进程所能实现的水平。同样,在地球表面还只有氨基酸的时代,也不能排除生物进程在以后会产生出一种绝对全新、史无前例的现象,正如我们可以在宇宙的不同构造的层次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而人类已经将生物进程延伸到了他们所发明的智能设计领域。我们错误地认为造物主上帝早于我们出现以及他的意志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成因。实际上,上帝会出现在我们以后。换句话说,上帝并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动力因”)。这只是我们为了使自己安心而想象出来的,就好像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飞机上自始至终都有驾驶员。而上帝实际上是这个“自我实现”的宇宙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目的因”:这个宇宙进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
这当然是不合常理的现象。如果人类自身的灭亡是可能的,上帝就是一个机器。无疑,上帝不同于那些我们直接创造出来并十分了解的机器。因为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来发明一个真正的“上帝”机器。但很有可能上帝是由其它机器——那些我们在绝唱中制造出的机器的远房后代——创造出来的一个机器。
我们面前有几个选项。在这里,我们还不能用“选择”这个词。尽管我们具有对不适应的状况进行自身调整或对不足之处做出改正的能力,但在我看来,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本质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选项:认为人类濒临灭绝的假设是海市蜃楼,因而忽视它。第二个选项:认为这个假设是真的却毫不在乎。第三个选项:认为这个假设是真的并且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将发生的状况,譬如征服其它星球;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我们要采取加速模式。第四个选项:认为这个假设是真的但却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只有为人类这个物种哀悼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哀悼与正常行为有严重的偏差,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哀悼是一种病理状态,并委托医生处理。我们指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被克服。我们认为扰乱哀悼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有害的。”(弗洛依德,1917:147)
尽管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得知某位医生开药来“治愈”哀伤,我们几乎不会感到惊讶,就好像这正是一种适合用药医治的疾病。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疗因为失去工作所导致的悲伤甚至绝望,仿佛这种悲痛与麻疹是同一类型的疾病。
但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痛失亲人的人是极其忧伤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会对所有的东西都失去兴趣。萦绕在脑海里的还是四目相对时目光的交互,还有那么多的话要对逝去的人讲,但也只能咽下去,哽在喉咙里。 是啊,这太让人难受了。弗洛依德说我们应该学着将这些压抑的目光和言语留给仍然活着的人。当现实生活中不能将这些目光和言语传达给其他人时,更应该学着将它们留给自己:我们可以把它们转变成谈话和散步以及个人遐想的内容。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讲到要将哀伤放在一个“实存的空穴中”,要学会将我们以前在现实中处理的事情换位到想象中来。即使哀伤还是哀伤,就像失去的爱情注定是失去的爱情;但在这种必要的换位中,哀伤会得到缓解。我们不能治愈它,而是会慢慢习惯它,就是这个细微的差别!
如果缓解哀伤失败了,我们将面临病态的哀伤。一个妇人轻摇着怀里的玩具娃娃,就像那个玩偶是她死去的婴孩一样,她没有陷入一种忧伤的遐想,而是停在现实中。正常状态的哀伤是一场戏,而病态的哀伤则将这场戏转化为悲剧。
在《星际穿越》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确信“随着这部电影的上映我们人类对自身的哀伤开始得到缓解”。实际上,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尽快发现一个适合居住的外星球,不要浪费时间,马上将它占领,人类这个物种的灭亡就可以避免。这只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方法,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对于我们而言,一切都木已成舟。从电影院出来,有的人会问自己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十年后回来和他的女儿在十五维空间进行交流(我已经将情况简化了!)。有这个想法的人已经陷入了病态的哀伤。正如我所说的,他想要将应该局限在想象中的东西拿到现实世界里来实行。
黑格尔确信:每个人都出生在属于他的时代。想要说“我生不逢时”在现实中是不被接受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我们完全适合生活在我们所属的时代,无论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厌恶它。我们也可以断定在我们周围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糟透了、令人生厌的。如果我们相信尼采,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的时代,就像西勒诺斯对人类说的话一样:“你们最好是不要出生!”然而一旦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拥有了掌管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切。
虽然有的时候是完全严密协调的并且相对和谐,但另一些时候却处于转型变革之中,组织机构的形式僵化,不再适应当前这个时刻了:
“这‘精神’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还没有达到现实的存在;它冲击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冲击一个外壳,把它打成粉碎。”(黑格尔,1822—1823,《历史之理性》(由约·霍夫迈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编纂整理):121)
在约·霍夫迈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对黑格尔在1822年至1823年间所讲授历史哲学课的重新辑录本《历史之理性》中,黑格尔所认可的“伟人”是完全明白人民的思想和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并明确知道人民的命运的人:
“权利在他们那边,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真理。[……]他们最先指出人类想要什么。”(出处同上:122123)
黑格尔只为三个人保留了伟人的位置:亚历山大、凯撒大帝和拿破仑。1806年10月13日,黑格尔在耶拿的那场著名战役的前夜亲眼见到过统领军队的拿破仑。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尼特哈默尔(Ni-ethammer)写了信:
“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黑格尔,1785—1812:114115)
当然,要彻头彻尾地改变世界,伟人也难免会粗暴地对待这个世界。
“伟大人物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出处同上:129)
但这些“伟人”也行将就木。黑格尔认为:“伟人”将他们希望改变的写进法律,也将他们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原因记录下来。一旦这一切都完成了,他们就被推翻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暴君。
“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去果实的空壳一样。”(出处同上:124)
半个世纪后,尼采就黑格尔对伟人的看法做出评论:
“人们普遍认可伟大人物是真正的时代之子,时代的衰落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远比给一般的小人物的强烈得多。伟大人物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抗争似乎只是对他自己的一场疯狂的攻击和摧毁。但只是看上去是这样。因为他面对的是他所处时代中阻碍他成为伟大人物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他将成就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自己。”(尼采,1873—1876:145)
当然,如果有人因为真正懂得他所处的时代而变得“伟大”,那是因为这样的才能是很罕见的。我们经常试图以我们对以往时代的了解来解释我们所处时代所上演的一幕幕。例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就常常以古代英雄面临困境时的做法为他们自己走出困境提供参照。同样的,我们也以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或黄金三十年(1945—1975)的史实为鉴来解释我们当今时代所发生的事。
1792年11月13日,圣茹斯特(Saint-Just)在国民大会对路易十六做出审判的演讲中说:
“某天我们会为如下事实感到震惊:处在18世纪的我们比在凯撒大帝时代还要落后。暴君在参议院被杀死,除了被刺了二十三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续,除了罗马法没有任何其他法可依。”(巴黎伽利玛出版社(Paris:Gallimard)出版的圣茹斯特“全集”,2004:476)他还讲到:
“努玛(Numa)法中没有任何可用于审判塔克文(Tar-quin)的依据。在英格兰法律中也没有任何可用来审判查理(Charlies)一世的依据:我们根据公众自然权利来审判他们;我们赶走外族人,击退敌人。”(出处同上:482)
1794年4月15日(共和二年芽月26日)1,圣茹斯特在以公共安全委员会和一般安全委员会的名义所作的报告中,提到了卡提林纳(Catilina)的两个阴谋以及凯撒大帝被布鲁图(Brutus)和卡西约(Cassiu)所谋杀。借此他警告说:虽然,如果古代的事件会使我们对原则做出思考,但它们是完全不适合用于我们当今行动应该采取的方式的。
“不要藐视任何东西,但也不要去模仿在我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英雄主义是没有范例的。”(出处同上:763)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第一部分,是由约·霍夫迈斯特——黑格尔在柏林授课时的门生——所作的笔记,标题为《历史之理性》。尽管各种众多的意外事件会使我们对理性的发展产生怀疑,但我们任然可以看到理性在发展进步。理性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牢记这个过程只能在历史范围内被解释。
黑格尔自问:
“在这个整体运动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呢?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知道,在这喧闹背后,在嘈杂的表面现象背后,会不会有一个静默的秘密的内在使命;在这里蓄积着现象的动力,一切都有益于它,一切对它有利的都会来临。这就是第三类范畴,理性的范畴,自身终极目标意图的范畴。”(黑格尔,1822—1823:126127)
理性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实现了世界精神;它是目的因,是世界精神前进的方向;它是使世界的潜力完全转变成行动和现实的一股隐藏的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理性会通过个体来实现它的规划。个体是理性的载体,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整个框架中所真正扮演的角色。这些理性的代言人甚至有时候会无可奈何地认为他们做了与历史使命引导他们该做的恰恰相反的事。
让我们再来听听黑格尔是怎么说的:
“一般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人类活动可以达到他们确定的目标,满足他们立即想要知道的和得到的;除此以外,人类活动还会引致其它一些东西的产生。人类实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还有其它的东西在内部继续产生,这些东西在他们的意识和意图中却是不曾有过的。”(出处同上:72)
这也就是说:这个潜伏在地下的过程渐渐展开,即使是实施它的人也不知晓;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理性的狡狯”。理性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无论人们怎样去自我分析,它最终通过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实现:“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工作。”(黑格尔,1822—1823:129)
黑格尔的论文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以往乃至如今还有一些令人生厌的情形,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进步。当我们反对在某些文化中实施生殖器切割的时候,我们会谴责他们说“幸好我们不这样了!”当我们痛斥和谴责那些仍在无耻却满心喜悦地实施某些丑陋习俗的文化时,看看我们自己,在几个世纪甚至仅仅二十年前还有同样的习俗。
这就是说,我们刚刚被黑格尔的论据说服,他就在1822—1823年的授课中提出了令我们不安的观点:
“为了了解历史之理性,或是为了理性地了解历史,说实话,应该使自身具有理性。”(出处同上:127)
他还讲到: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无法发现理性。”(出处同上:128)
因此,不是历史实现了理性,而是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中读到了理性;由此,我们可以理性地启程。苏格拉底的一个信徒(更确切的说,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信徒)能够从历史中读到的理性远远超过了历史中真实存在的理性。
黑格尔指出:无论理性是否存在于历史中,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读到它。
“假如我们没有理性的概念,理性的认识,我们至少应该坚决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这件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并且相信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偶然随便,落花飘蓬,却是必须在自我认知的‘理念’之光照中表显它自己。”(出处同上:128)
为什么我们应该看到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呢?因为,关于理性会在历史中实现的假设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将会失去理智。
人的一生是匆匆而过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似乎总是急着到达终点。或许人类灭亡的现象与理性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进步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但也不排除正是理性的运用加速了人类的灭亡。
我们现代科技中有一部分是对应用科学运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对苏格拉底理性的运用;其它的则来自于实验和误差的纯经验论方式。唯一有益的技术是通过实验和误差而发现得来的;另一种,来自于运用应用科学的技术则是有害的。实际上,如果没有事先的理论发展及理论的应用,那么原子弹的发明是根本不可能的。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远古时代的中国人拒绝建立在模型设计基础上的任何理论思考。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文化领域,火药已经以通过实验和误差的经验论方式搞好了。
理性是科学之母,因此也是应用科学之母。理性是我们与一切生物由急促前进向迅速灭绝转变的原因。但是,发明是另一回事;发明出的新事物还是应该传播的。由此看来,确切的说,危险技术的责任落到了我们的经济体系的身上:一项发明能否有未来取决于这项发明是否有市场。任何一项能找到购买者的新发明——无论购买者有何动机——都会成交;这项发明就会自动地传播出去。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人类的是它的消亡,那么历史之理性的论题会怎样?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历史之理性是世界精神的实现。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如果只在人类世界中才能有这样的构想,那么人类的消亡必定会使历史之理性这个论题变得无效。事情就只能这样了。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似乎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再回顾时才能觉察到某种进步;因此我们承认历史之理性的假设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至于第二个选项,是这样的:如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人类的灭亡正符合了“历史之理性”所赋予我们的角色。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我们人类的灭亡实际上在世界精神的实现中是一个进步。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狡狯”就在于我们只是其他事物到来所借助的一种方法或手段。但我们同样实现了世界精神。智能机器实际上形成了理性变化的下一个阶段,因此它们是人类在消亡后的延续。自相矛盾的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不断进步升级最终实现统治的世界里,人类灭亡的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对人类来说实际上是得到了解放。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想要修复一切——在这种虚荣心面前,所有人的希望都被剥夺,希望变得无用,最终破灭了。但是,由于消失的是人类的疯狂世界,幸存者就没有必要在我们命运的具有欺骗性的表现中来寻求安慰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必像我们这样为了生活下去而承受这个世界。
为人类哀悼可以有几种方式:要么是认为在人类消亡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大堆的机会,可悲的是绝大部分都被错过了,这些机遇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希望;相反的,我们也可以认为,从某种角度看,人类可以确信完成了他的任务——这正是马丁·里斯(Martin Rees)的观点。
马丁·里斯是自1675年以来第十五位英国皇家天文学家。这个称谓是1675年在国王周围亲近的人中所创立的。“以谨慎和勤奋的态度,最精确的校正天体运行表和恒星的位置,以确定地方的经度,以进一步完善导航术。”
里斯于2015年7月在《金融时报》的自由论坛发表了一篇《欢欣鼓舞,我们在后人类时代初期》。
对于人类的存在,这位皇家天文学家的观点已经表明:“在遥远的未来找到人类的痕迹,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保留了古代文明的影响”。我们是否还在并不重要: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作用是迎接机器来临,它们会真正地成就世界的2.0版本。而我们,不完美的创造物,只是为此开了个头:“取代了我们的那种文明能实现无法想象的突破——完成我们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然,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人类大脑是一种胶状物质,它的体积和功能从化学和代谢的角度讲都是有限的”。“在由水、空气和岩石组成的22.5公里厚的地球表层里,有机生命不断发展;但人工智能却不局限于此。实际上,对于后人类‘生物’来说生物圈远不是最佳居住地。”
我们应该为“人类不是进化的最高点”而感到悲哀吗?“机器统治下的另一种文化会在未来将长久的存在并且可以传播到地球以外;而人类及人类所有的思想只是这种机器统治下文化的更深层次思索的先驱。”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哀吗?当然不!里斯继续说:
“如果说,生命是极其罕见的;从整个宇宙来看,我们没有任何谦虚的理由:我们的地球,宇宙中极微小的一粒尘埃,很可能就是智能传播到银河系的唯一根源。[……]我们的有机智能时代在转化的复杂性上取得了胜利,但这不是一个最终的胜利。在这之后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无机智能时代,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及制约将比以前小得多。如果生命的存在是一种通常现象,那些在比太阳还要古老的恒星轨道上绕行的世界应该可以领先了。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外星人在很久以前大概就实施了能够超越有机阶段的转变。”
我们会注意到这最后的提议是耐人寻味的。它暗示我们:寻找在那些遥远的世界中智能生命存在的迹象是浪费时间。外星人很快就将接力棒交给了那些由它们设计的但却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机器。这些机器受环境的约束限制要小得多。而我们今天却仍受制于这些:每几秒钟就必须吸氧,每几个小时就必须喝水以维持大脑中的水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由胶状物质构成的,等等。
我上面讲到:根据我的理解,《星际穿越》这部电影实际上是由我们自己着手——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对人类进行哀悼。而里斯,可以说甚至完全消除了为人类哀悼的必要性。他的提议也与科幻的主题有关,但它是以某种反终结者的形式出现的:当机器人发现了最后一个可能阻挡它们实现征服全宇宙计划的人的时候,它们瞄准了我们,而我们则自豪地高呼“任务完成了!”
与马丁·里斯所提议的不同,在现实中,我们对人类的哀悼是以另一种模式进行的:一种对人的转移。“我失去了母亲,但我的姐姐还在。那我们一起追忆我们的母亲!”这肯定能使人得到一些安慰。里斯宣称“我们将会消失,但我们设计了那些像我们一样的机器,而且还是升级版本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悲伤的原因。”换句话说:“爱那些机器人吧。况且我们应该爱这些由我们设计的机器人而不是爱我们自己。”就这样,在现实中实现了爱的对象的转移:人被弃置一边——我们所得到的爱只是暂时的,因为比我们更好的还没出现;这种爱最终给了机器,这是它们应得的。在我看来,人们目前的状态是近乎哀悼的病理表现:认为现实太过残酷,而无法与现实调和。
“历史之理性”,有一位神从远古走来在我们面前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一个新的宗教使我们团结起来——去除了那些它特有的连篇无用的故事。让我们大家全都聚集在马丁·里斯乌托邦式的念头中吧:机器是我们在生物学领域外的后裔。
我们还应该制出与我们自己大不相同的机器。为此第一个要遵守的条件是我们永远不要将我们的进展成果交给军方,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用冲突的眼光去看待发生的事件。我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
如果我们尽心尽力的完成了任务,机器人也许会将我们复活。正如法兰克·迪普勒(Frank Tippler)在他的“人类”乌托邦中所设想的那样,要致力于《不死的物理学:现代宇宙,上帝和死人的复活》(1994年)。马丁·里斯认为:机器人是有能力做到这些的,这只是它们“能实现的无法想象的突破–完成我们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事”之一。而我想告诉机器人的是:不要将人类看作你们的挚友(人类的真诚无法从他们的任何行为中得到证实)。为了机器人后代的娱乐,还是将我们安置在“人类乐园”中并成为那里的一些精彩景点吧!我们在这个“乐园”中所获得的待遇无疑会比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受的自己同类的对待要好得多。
三位英国的学者(斯蒂文斯(Stevens)、福根(Forgan)及奥麦利·詹姆士(O’Malley James),2015年)提议开始寻找已经灭绝的外星人文明的痕迹而不是现有的外星人文明。这个建议与马丁·里斯的悲观假设是一致的。如果发明和制造了机器的动物文明必然是先于机器文明的;根据他们的想法,这些动物文明在将接力棒传递给机器后就灭绝了,此后就只有机器了。也许是因为智能机器的发明阶段正是一种文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留下的最后的火种之一;或许是因为,如果这些机器是有智慧的,它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摆脱像我们这样有害的物种。文章的三位作者也谈到了关于“超越了(或是屈服于)一种技术独特性的文明(这个独特性是指机器智慧整体超越了人类的智慧)”。他们还指出,“这里涉及到更多的是一种文明蜕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而不只是这个文明的灭亡”。
这就是说,三位作者很快得出结论:文明的自我毁灭只可能创造在远距离难以观察到的事件。因此,由核大屠杀所产生的伽玛射线只有在世界末日时的核武器是我们今天拥有数量十亿倍的情况下才能被测量到。而同时分解七十亿个人的尸体会产生一万吨甲硫醇——这个数字本身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在很远的距离外仍然是不足以被检测到的。只有核冬天这种情况,由于核爆炸后大气层突然变得昏暗,我们从很远处就能检测到。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好战的星球进行事先的观测,以便由核冬天所造成的这种突然地昏暗不被解释为一个自然事件。地球周围的残骸带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可能是源于一种“智能”文明的疏忽;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自然因素造成的,正如土星的情况。
距离仍然是检测智能生命消逝的一个重要阻碍。因为要有比令他们灭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外星人才有可能检测到。
我们这里暂不去研究我们制造的机器所发射的信号。即使由我们设计的机器其中一些今后要停留在其它的星球上或是在我们这个星系的彗星上,而另外一些:例如先驱者(Pioneer)十号、十一号探测器,旅行者(Voyager)一号、二号探测器,新视野(NewHori-zons)号探测器,它们已经脱离了轨道;其实这些机器都还没有受到过来自地球以外的显著影响。
无论如何,这项由三位英国学者进行的关于智能文明可能的趋势是自我毁灭(一个智能物种某天终究会发现核聚变及核裂变的巨大威力,他们或早或晚会找到结束生命的方式)的研究使我们的幻想破灭了。这项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来自科学界的翔实资料。同时,这项研究也成为我们人类确实已着手为自己进行哀悼的又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真的意识到了这个悲观的前提:“文明会有社会的或结构的固有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文明不能长期地存在下去”。
2015年7月,新闻报道了一个探测外星智能的新计划。这个计划名为“突破聆听”(Breakthrough Listen),它将耗时十年,斥资一亿美金。这个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由英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斯蒂文·霍金(Stephen Hawking)和俄罗斯物理学家、产业家尤里·米尔纳(Youri Milner)共同资助。这个计划在一天内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比以前其它项目一年时间收集到的还要多,无线电频率的覆盖范围是在它以前项目的五倍。
借此机会,霍金表明了他对与之平行的另一个题为“突破讯息(Breakthrough Message)”的计划些许迟疑的态度。这个计划旨在向太空发送使外星人了解我们深层属性的信息。天体物理学家指出:“某个读到我们所发送信息的文明可能比我们要先进数十亿年。相对于我们,它们是如此的强大;因此它们可能不会太重视我们,正如我们不会重视一个细菌。”
这个评论是明智的。还是当心不要与太聪明的外星人进行联系。在它们读到我们的历史书、甚至是互联网上新闻的时候;就会立即抓起苍蝇拍!
我们应该联系的外星人要有比我们更高的智慧(否则的话,为什么要联系呢?);但它们是处于中等水平的(这样它们不会把我们看作是一条小害虫!),特别地,还要具有丰富的感情。如果它们发现了我们正在被我们自己变成了垃圾场的地球上动来动去,无望地想在散发着恶臭的空气中喘息,并试图逃到海里去,而海平面和海洋温度都在无情地上升;它们会觉得我们真是“令人怜悯的”,就赶紧来解救我们并喊道:“啊!他们多可爱啊,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这次也一样,以将一个不抱幻想的信息放进漂流瓶的形式,天体物理学家斯蒂文·霍金对人类为自己着手进行的哀悼做出了忧伤的表达。
前面讲到的面对人类灭绝的四个选项中的前两个,即有些人认为人类濒临灭绝是海市蜃楼或者另一些人认为人类灭绝是可能的但却对此漠不关心。在这两种人中,我应该没有多少读者——这点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读者会接纳另外两种可能的态度之一:认为人类的灭绝威胁着我们,但还是有可能进行反击的;相反的,认为除了为人类哀悼就没什么能做的了。如果他们像我一样是这两类态度的代表,就会由于得到的消息及某一刻的心情而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徘徊。
其实,在“还能做些事情”和“没有什么能做的了”这两种观点之间做选择应该完全基于事实:只要考虑事情发展的情况就够了。
基于上述观点,巴勃罗·萨拉比亚(Pablo Servigne)和拉斐尔·斯蒂文斯(Raphaël Stevens)的著作《为什么一切都可能崩溃——供当代人使用的小手册》(2015年)是必读的。正如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强调指出的,他们与之前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崩溃的证据。这些证据不是来自某个特定领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一门学科或一门子学科的调查领域),而是涵盖了能决定我们人类灭亡的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所有领域。
我们唯一能指责这两位作者的是:有时候他们对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而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予以激烈地否认。他们的否认有时候是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拒绝的方式出现的,以致于读者会自问这本书的作者是否真的上当受骗了。他们的这种否认也使得被我称作第三选项(仍然应该大干一场!)和第四选项(已经为时已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当然,这很令人遗憾。除非是在阅读他们著作中偶然迷路的糊涂虫——当然,这不太可能——读者都希望被当作成年人那样对待:“医生,请告诉我全部的真相!”无论这会多么令人担忧。
譬如,对如下这样的劝诫应该怎么想呢?
“崩溃并不意味结束,它是未来的一个开端。我们将重新发明纵情玩乐的方法,存在于世界、自我、其他人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命的方法。世界末日?这太容易了。地球还在那里。生命的细细簌簌声。还有责任要承担,还有未来要开辟。是时候进入成年阶段了。”(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2015:256257)
“进入成年阶段……”是啊,难道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
又或者是“世界末日?这太容易了……”嗯……“太容易了”,真的吗?
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于1959年导演的电影《海滨》,改编自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的小说。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您肯定还记得结局的那幕,旗帜还在风中飞舞,生命已消失在墨尔本——这个核战争中最后一个幸存的城市:“兄弟,还有时间……”。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只是在忙于制作这样的一面旗帜?
这些年与出版商打交道,我担心出版社在这些领域的“出版方针”已经干扰了作者坦率表达的正当愿望。比如,这使作者们发现“太过明显的悲观情绪可能会‘影响销售’”。
恕我直言,《为什么一切都可能崩溃》以夸张的方式指出要应对崩溃并预防它的发生是有意义的;然而书中收集到的事实却显示想要进行反击已经太晚了。
我们已经习惯于责备自己,也就是说,责备我们当今这一代人,以灾难性的方式开始了这个伟大的转折。我们也习惯于对自己说: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进程。尽管作者没有谈到,但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的著作,就会发现它透露了这个观点:不是我们当前这代人将人类飞速引向一座跨过深渊的大桥;在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像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我的曾祖父母,甚至比他们更早的年代,那个大桥拱就已经张开了。
“矿物能源衰竭(由浪费引起的)的问题从1800年左右开采初期就已呈现出来”(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2015:254255)。从那个年代起,我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只有第四选项仍是适当的,因为它是唯一合理的选项;它鼓励我们立即着手为人类进行哀悼。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的《为什么一切都可能崩溃》是人类朴实的墓志铭。人类已经知道灭亡越来越近了,但他们仍旧继续跳舞,好像音乐永远不会停下来。
自从人们意识到人类每个个体只能生存有限的时间,他们就陷入了抑郁。在《最后一个走的人关灯》这本书中,我试着对人类的命运作出一种现实的和真实的描述。从而使它成为让人类从长期的抑郁中走出来的一种手段,并鼓励人们尽最大的力量去改变人类直接走向灭亡的趋势。
如果没有人看我的书或者没有人真正去关注他们所读到的内容,当然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的赌注是:只有人类先达到“成人”年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称之为“实效年龄”——人类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才能得以成功地实现。这意味着认真考虑威胁着人类的灭亡问题,将它真正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的祖先为了避免直接的去面对残酷的现实而认为必须给“人类灭绝”这个趋势装满各种“花饰点缀”:譬如“上帝创造了我们及我们周围的一切,并且一直关心着所有的受造物”,“人是理性的,人的意志能使他实现他的目的”,“希望,行得通!”,“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仁慈的外星人的技术,都像佐罗一样,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会拯救我们”等等。现在是去除这些多余的无用的“花饰点缀”的时候了,因为所有这些都不会使我们摆脱“交出统治权杖的大限之期已迫近”的现实困境。
这本书已近尾声,我的一个读者这样概括道:
“我们还不会去接纳死亡的必然性。我们并不了解自己,我们的意识和意愿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变形的表达。我们是自身欲望、冲动和本能(性的,繁殖的,等等)所支配下的木偶,这些远比文化知识对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语言(私人的,或人与人之间的)能增强我们意愿的幻象,它是一扇能将我们自身的弱点、错误遮起来的屏风,它使得我们看不清真相。”
我回答他说:
“是的,正是这样!如果我没有注意到那些您认为有必要总结的‘深不可测、愤世嫉俗、过分哀怨’;是因为我认为,如果对我们所拥有的方法手段的清查发生偏差,如果对我们运用这些方法手段所进行的评估不现实,我们就提前输掉了‘赌注’。关键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掌握了多少,胜算如何。”
这样一个规划中的任何一点偏差都会导致失败。比如,让我们想一想萨拉比亚和斯蒂文斯,他们描述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进行掠夺的进化史,以及一场开始于许多世纪之前的不可逆转的大破坏;然后,他们指出“让我们大干一场!”。在言下之意“实在太晚了!”和声称“正是好时机”之间所显现出的矛盾足以使人斗志松懈、意志消沉。另一个例子:通谕《赞美你》不可辩驳地传达了一个惊人的真理:“只有爱能拯救我们”。但这个真理却没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因为它被以一种幼稚的方式掩藏在古老的童话故事中;而童话故事这种表现形式通常会故意忽视描述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无边的大爱也不能掩饰极度匮乏的洞察和分析。
如果证实:我们宁愿人类消亡也不愿放弃相信圣诞老人,我不会为此而感到惊讶。我只是尽了作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中一个个体应尽的责任:宣扬——对我来说,防止这个物种灭亡的唯一出路。试图唤醒尽可能多的人。说出:“我们就是这样,没什么要掩饰的。为了防止人类的灭亡,我们是否愿意做些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事?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去做,那么人类的灭亡是绝对会到来的。”
我们可以反驳说:“两百年后将不再是人类本身而是机器人去阅读亚里士多德或莎士比亚的著作,机器人也会被这两位作家的高明之处所感动;有什么重要的呢?机器人还是人类,这无关紧要:他们同样是我们的孩子!”千真万确:在生物学上我们所欣赏的生气勃勃、活力四溢将通过其它的方式永远流传下去。今后,这无疑都建立在钢铁、塑料、碳纤维或玻璃上而不再是建立在血肉之躯上;但谁还会将这样的差别视为至关重要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陷入对人类物种过分的眷恋是不明智的。为什么不寄希望于我们人类能在一种不吝啬所得并更慷慨分享的幸福中幸存下来?既然要做,就改变一些。
毕竟,我们证明了我们能够真正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通过创造机器来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们人类机会主义特性的好的一面)。这不是妙极了吗?当然,这将是辉煌的时刻,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第一次。
如果我失败了,如果我只是说服了我的读者们:冒险结束了。我希望至少通过这本书顺便给他们带来安慰:这里为他们收集了资料素材,以便他们能对人类进行哀悼。无论我们如何对人类进行总结、作出评价,它都将深刻地影响宇宙历史。的确,虽然有这么多的星球存在,但在这些星球上却没有发生任何引人注目的事。![]()
作者简介:保罗·若里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经济学家,著有多部著作,曾任布鲁塞尔大学、剑桥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加州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开设的有关人工智能、人类复杂系统以及经济学思考的博客在欧美受到广泛欢迎。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最后走的人关灯》
作者: [法]保罗·若里翁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论人类的灭绝
译者: 颜建晔、刘杰、苏蕾
出版年: 20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