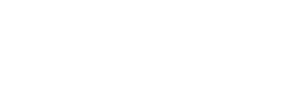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在鹤岗

过去二十年,我们评价和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富裕,总是最先提到这座城市的房价,于是鹤岗成了“反面”,成了众矢之的。我们评价和衡量一个城市是否与时俱进,又总是最先提到这座城市的数字化程度,于是鹤岗成了尾部、末端。而现在,房地产、互联网速度渐缓、慢了,没有什么拉着我们奋力前进了。我们是否可以放下对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迷思,重新寻找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准呢?
被架空的城市
去鹤岗之前,我读了些报道。资源枯竭、人口外流、衰落、破败,我从网络上的文章看到这些字眼,想象这座城市就像一个醉醺醺的中年人,身上笼罩着失去的阴影,它失去了资源、财富、失去了年轻、活力,面对没有目标的生活,只能孤独地留在原地,消磨时间。究竟那样的形象是如何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很难说没有受到电影和其他媒介的影响,就在导演耿军的电影《东北虎》里,人物就是这样的状态,他们做着没用的事,然后不停感叹“又荒废了”。
《东北虎》的大部分场景都在鹤岗取景:漫长的冬日,摩托车从空旷的雪地上碾过,眼神落寞的人坐在炕上,面对一桌子被剥去的花生壳和将空的酒瓶。大众媒介塑造了我们对城市的印象和认知,它们在我们的脑海里印造出一副图景,然后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现实。
还有另一副图景可能更为深入人心,关于这里的房价。两千或者三千一平米,也就是说,只要二十万到三十万,你可以拥有一个一百平的房子。你不需要背上沉重的房贷,不需要必须组建一个家庭来分担高昂的房费,也不需要担心老了以后无家可归。
2018年,一个网友在百度“流浪吧”发帖讲述了他去鹤岗买房的故事,然后媒体重新将视线移到了这座城市身上。一座城市的落寞、老化都被再次放到聚光灯下,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宣扬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慰藉。它给了那些对生活丧失希望的年轻人一个家,也就是一个房,并且它提供了一个精神空间―—不论你多么失败落魄,来鹤岗吧,生活还是过得下去!
在佳木斯机场,我跟我的同伴们一路开车到鹤岗。这座城市被天空包裹着,一仰头,就能看见云,远处的云形态各异,你可以欣赏它,近处的在头顶之上展开,像是对这里的庇佑。绿色的草地、沥青的马路,所有的东西都是鲜明和界限分明的。
到达的第一天,我的同伴们就组团去看房了,出于对物美价廉之物的欣赏和好奇。我也开始在短视频app上挨个看那些卖房博主的视频。他们通常会拍装修后的屋子,那些房子看上去的确精致,通白的墙体,客厅点缀几颗落地绿植,墙上挂着金属框挂画。博主介绍说,这是花了三十万左右装的效果。花三十万买房,再花三十万装点,尽管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我还是会感到一丝惊讶。在互联网这座舞台上,诸多事物被制造出来不是以供使用,而是以供观看。他们甚至可以脱离现实的城市而存在。当视频中,卖房博主将镜头扫向落地窗,窗外一片晴朗,远处还有树林,有那么几分钟,我恍惚间觉得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处所。
这些卖房博主们似乎也脱离了城市本身而存在着。他们大都是在2018年“鹤岗低价房”变成新闻以后开始从事房地产行业,他们的关注者和客户大都是外地人,他们也不被本地的网红公司所看重,尽管他们发一条短视频就有成百上千的点赞量,他们的影响力足以辐射全国,但一位鹤岗的网红公司老板说:“他们压根无法带货,甚至不如那些才艺博主,因为他们的粉丝买了房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除了那些精致的房子,鹤岗的另一面在“直播鹤岗”的账号里。那是鹤岗电视台的官方账号,全天候直播,似乎是一个监控摄像头的角度,镜头总是对着某一条街,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各式各样的车来回穿梭,小汽车、公交车、摩托车、吊车,它们保持着平稳的节奏在城市里工作,人隐匿了起来。在这些远距离的俯视镜头里,我看到了这个城市原来的样貌,一个秩序井然的巨型工厂。
三十年前,在煤矿的鼎盛时期,工厂还未衰落,这种秩序是更直观的。在一张三十年前拍摄于农贸市场的老照片里,售货员戴着统一的白帽子,消费者穿着颜色差不多的衣服,人挨着人,看不清人,但看得清整齐的队列。
三十年后,我在市人民广场上再次看到工厂遗留下的印记。在一个两万多平米的广场上,自发来跳广场舞的六七十年代的老人们,不自觉列起了阵,方的、圆的,从东到西,他们占据了整个广场。工工整整,边界清晰,看一眼便能知道他们分属于哪个广场舞队,如同一场正式的集体演出。

闯入者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鹤岗是很困难的。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想干体力活,也不想做销售,在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作可做。打开鹤岗发布招聘信息的公众号,偶尔能看到一两个科技公司的招聘广告,他们招募客服岗位。当然了,这里的“科技”公司只是与科技有关的公司,他们是互联网的服务者,不需要掌握科技,在这里工作,你需要的技术只有一项:会打字。
一天早上,我跟随HR微信发来的指引,走进深藏于小区中的一家科技公司。公司楼下是家发廊,隔壁是家中医按摩店,早上九点,十多位客服坐在他们的电脑前,盯着屏幕上的淘宝对话框,敲击着他们为自己配备的机械键盘。 我走进来,公司经理什么都没问,她已然默认造访者来这里就是来面试的。她直接打开“金山打字通2016”叫我试试。
我在打字测试软件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句子:
“好哒呢亲爱的,这边收到了您迫切的心情,这边一定给您加急发货。”
“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深感抱歉。”
“实在不好意思,您看我这边给您申请一些补偿可以吗?”
我面对电脑,不用调动任何智力或情感,只有手指在运动。看着显示屏左下角不停上涨的数字,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打游戏的兴奋感。只要我能保持住这个节奏,随着时间的增加,速度就会上涨。十分钟后,经理走过来,打断了我:“挺好的,可以了。”数字停留在了每分钟74字。从停下来的那一秒起,数字开始下降了,一时半会儿,我的目光还无法从那里移开,然后我听到经理说:“你的速度挺快的,你可以试试售前。”
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没有关于学历、年龄、婚姻状况的问题,只不过十分钟,她就开始交代上班的注意事项了。直到我说我不是鹤岗人,经理停了下来,她面露难色:“估计你也干不长,我们不想招短期的,三月两月,这边刚学成熟,你扔下店走了,我们还得再找。”
鹤岗人似乎习惯了用一种更为长久的时间尺来标记和筛选一切。他们想要留得住的,而不只是暂时可用的。那些迅速攻占下沉市场,渗透力极强的互联网产品进入这座城市也要接受这样的考验。共享单车来过,后来全清了,随意停放的单车影响了城市的干净;在线麻将来过,后来市民们加大了赌注,它成了赌博而非娱乐,就被取缔了。大众点评也有,但没有商家经营它;出租车招手即停,不需要打车软件来进行资源配置;司机也都通晓城市的每一条马路,不需要电子地图来提示最短线路。
在这短短十年,这里有过不少雄心勃勃的科技创业者带着他们的产品,试图闯入这里的故事,也有很多互联网文化同集体工业文化的碰撞带来的,类似于当创业者提出“孵化器”的理念时,被当地官员误以为是孵化小鸡的笑料。
留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找到了一位。我在一个小区的底商门店见到了他―—鹤岗互联网行业最重要的人―—刘永朋。他的公司会承接程序开发项目。门店临着街,一进去,我看到被玻璃分隔出的三个格子间,其中一间是刘永朋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蓝色商务格子衬衫,坐在会客室里,面前的茶具盘占据了整块桌面。这里就算作他的办公地了,另一个据点在郊区,他不常去。2017年,由市政府牵头修建了一块“互联网+”基地,近4000平方米,刘永朋被政府任命为基地的董事长。
刘永朋曾经在百度北京总部做产品经理,他从小在鹤岗长大,直到大学才离开去了佳木斯,读大学时在BBS上认识了几个程序开发的好友,没过几年去了北京,进入百度工作。2017年,他回到鹤岗开始互联网创业。截止现在五年的创业历程让他总结出鹤岗的生存之道:“(产业)不是分头部、腰部和尾部嘛,实际我们做的是一个尾部的工作,就是当信息比较滞后的时候,一味地追求像深圳那种起步的东西,从人工成本和投入上都是消耗太大。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靠量取胜。”
这些尾部的工作其实就是搬运。这些搬运工作包括复制淘宝店铺,拼贴企鹅号文章。30个人可以管200家店铺,50多个人可以维持两百多个企鹅号,一个人一天可以拼出五篇企鹅号文,一个账号一天收益近两千。他们从网上找来文章,再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唯一的要求是保证重合率不超过85%。他们制造合规的产品,而唯一的质检员就是互联网审查员。
企鹅号和百家号最受欢迎的时期,也是刘永朋公司产能最高的一段时间,后来短视频夺走人们的注意力,刘永朋自认为错过了入局的机会。当他预备改变时,“短视频赛道已经很拥挤,竞争不过了。”只依赖一个互联网产品进行生产是有风险的。相比之下,本地客户要稳定的多。刘永朋帮鹤岗的商家做过促销小程序,在微信没有投票功能之前,他也做投票小程序。小程序的框架都由他写成,员工只需要做一些填充。
公司真正步入正轨是去年的,他有了稳定的业务。他为鹤岗市和双鸭山市搭建疫情数据统计平台,这是能放在公司案例PPT首页的那种受到绝对认可的项目,更是一座“富矿”。刘永朋给鹤岗兴山区政府搭建数据平台,赶工一个月完成,之后还要不断填充新的功能。防疫工作的主体负责人是区政府,一个区就需要一个系统,鹤岗市有6个市辖区,还有临近的双鸭山市、伊春市,它们都可能成为产品的买单者。
刘永朋搭建的疫情数据平台并不复杂,主要是搜索和上传的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数据。使用者是区内所有的基层工作人员。在这个深蓝色的页面上,能看得到全区人口数、党员人数、疫苗接种人数、返城人数实时更新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来自人口普查以及健康宝实时上传,开发者所做的仍就是搬运,将数据从Excel表格搬到一个H5网页中。系统正在向一个综合平台发展,刘永朋说,他们正计划将公安系统、党建系统的数据都集合到一起。
作为一个习惯了动用大脑的工作者,我对搬运这种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敌意。特别是这些数据搬运工,他们做的不过是些复制粘贴的工作,毫无创造性。而我们这种创作者跟那些互联网搬运工甚至是水火不容,因为我们遇上他们总是因为被抄袭、被侵权、被盗取。但靠搬运数据养活公司的刘永朋看到了这其中的巨大意义。搬运是一种整理,原来的户籍信息和人口统计里,那些重复的、被遗漏的、不完整的数据都被系统找了出来,并做了大量矫正。而最新的准确数据和旧数据之间的误差能解释很多问题。
复制搬运是这座城市公认的经营规律。鹤岗最大的咖啡馆绿思咖啡在一个市开了四家店,每条商业街都有一家本地人创业的奶茶店,多走几条街就会发现这家本地奶茶店的另一个分店。似乎那些大城市有的消费品在这里都能找到平替,没有必胜客,但有九块九的披萨和炸鸡。没有瑞幸,但有蜜雪冰城旗下的咖啡品牌“幸运咖”,一杯美式咖啡可以卖到七块钱。

忙碌,为了充实
每个生活在此的人都跟我说,“鹤岗其实挺好的”“鹤岗只是这几年不行了”。语气中有种满足感,可又并非全然感到满足。这个城市填满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欲望,但冬天滑雪,夏天钓鱼的安逸似乎又带来了不满足。
鹤岗市中心有一家名为“比优特”的超市,这是鹤岗最大的超市,最早只是一家6平米的化妆品门店,而现在,它所在的商业大厦叫“比优特时代购物广场”。由于比优特在鹤岗的产业太多,市民们平时的称呼会直接省略“比优特”三个字,而是叫“时代购物广场”。比优特从鹤岗起步,向周边的城市辐射。鹤岗、佳木斯、黑龙江几个城市现在共有80多家比优特超市的分店,成了“中国连锁百强”。
这家超市看上去没什么特别,除了办公室墙上贴满了规章制度和报表总结,柜子里桌子上,到处都是A4的表格。来鹤岗好几天了,只有在这家超市,我才感受到时间的紧张。员工们人手一块智能手表,忙起来的时候,甚至没有时间掏出手机。
一位企业微信的员工告诉我,比优特在企业微信上开发了两百多个功能,对于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来说是很罕见的。他们开发的功能并不复杂,都是类似查库存、查销价、更新商品状况、审批商品的任务。以前这些任务需要理货员挨个清算,记在表格里,或者录入单独的系统,而现在这些系统被整合在了微信上。这种开发能力是怎么来的?仍旧是搬运。尽管这些小程序本身不是产品,无法获利,但它的工具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
当店长说她的员工很适合现在这个“团长”的岗位时,那是对一个人的真诚赞许。当团长将最新的促销商品发在团购群里,她将这看作传递一个好消息。当这里的员工讲起忙碌,他们是平和的,忙碌填充了他们那亏缺的精神上的满足感。忙碌是为了充实,而非刻意加速。
向上、进步、发展,是过去二十年我们奉为圭臬的价值,但鹤岗不是这样,它习惯了缓慢和自足,整座城市就像是被定格在了某个时间点:可能是20年前,当时互联网还是个新鲜的名词,腾讯、阿里巴巴都还不存在,鹤岗就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人肉搜索事件,一个女人拍摄虐猫视频,上传到了互联网上以后被网友扒出了真实信息。那时候,刘永朋买了他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万块,跟现在的价格差不多;也可能是15年前,淘宝电商刚刚开始走上坡路,刘瑞铭出于兴趣,开了家淘宝店卖女装,但她看重的只是鹤岗的实体店,她从不为经营状况发愁,那时候花几千块钱买大衣的人,在鹤岗有很多。
当站在虚拟和实体的分岔路口,选择重点经营淘宝还是实体店时,刘瑞铭选择了后者。她错过了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捞金的机会,这似乎是个错失财富的遗憾故事。二十年后,她和别人一起创业开整形医院,合伙人信奉扩张和速度,试图占领市场,一年内在黑龙江开了五六家分院,而她相信经营和稳健,她再次选择了退出,这个故事现在显然不会再令人遗憾了。
今年,她又重新开了家电商公司,二十多个员工。我走进她的公司的直播间,小格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把椅子,一块纯色背景布,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打造了两个直播间,安上直播设备。直播时,也只有主播和场控,两个人在这里工作。
她没什么发展壮大的野心了,她唯一的希冀是,能从卖别人的产品变成卖鹤岗的农产品。因为这个时代是赢者通吃的,鹤岗的大米会被五常的大米厂商收走,掺进他们的袋子,再打上“五常大米”的标签。“鹤岗的大米特别的好吃,可是它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包装,自己的品牌。”她说,她也想过跟杭州广州的电商公司合作,但没人愿意卖农产品,农产品的利润只有10%-15%,但化妆品、衣服的利润能达到65%。更何况,从这里发货的快递费还贵。无论如何,这不是个取巧的买卖。
棚改房
一天晚上,我打车去了鹤岗普陀山,我预备在山上走一走,但下山成了麻烦事,我拜托出租车司机等会来接我,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司机表示可以等下山后一起付车钱的意思。二十分钟后,我在约定的地方上了车,车里还有一对母女,女儿四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这对母女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
司机将这对母女送到了鹤岗棚改区的楼群附近,这里是鹤岗房价最低的区域,网络上那些两万块钱一套的低价房便是指这里。这里像是一片原野上横空竖起一大片楼宇,工工整整排列在此,除了楼什么也没有。
母女俩下车后,司机开口说话了。他说,这里住的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规整的楼房墙体遮挡了这里的本质,这其实是鹤岗的“贫民窟”。每个城市都有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也总会聚集在某一块区域。只是我想到我曾在网络上看到对于鹤岗房价的分析,网民们煞有其事地分析鹤岗房价低的原因,媒体也在一旁推波助澜。2019年某媒体发文《实地探访鹤岗楼市真相》,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棚改房太多了,才导致商品房无人问津,所以房价上不去。按照经济学规律,这是一个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结论了。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偏差,我们将一个地区的房价低归罪于这里的“贫民区”。当对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商品市场发生冲突时,我们关心的是市场,是房价,而不是社会保障。
出租车慢慢驶出棚改区,要经过一大批荒无人烟的田地,才能进入市中心。夜晚,整个城市更是空荡荡的了。这是座作息时间过分健康的城市,不过晚上十点,店铺关了、灯光灭了,就连经过最热闹的烧烤店,也只能听到些细碎的说话声。司机说,他送完这单也要回家了,他的家就在市中心,晚上九点多,已经没几辆车在路上开来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