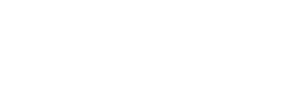行走改变世界

2022年,我的飞行记录是零次,为数不多离开北京的两次出远门,都是在夏天,一次是去乌兰布统大草原,感受了一把草原的辽阔和粗粝;另一次是去了烟台、威海,打卡几处小红书推荐的当地风景名胜,结果如你所料。其他时间,只能围着北京理性的环路兜兜转转,这样的日子让人心里发闷,就像这场大流行一样,我经常盼着生活能另起一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假如没有互联网,过去三年的时光可能会更为艰难,在方舱中的病患、飞驰在街头的外卖小哥、地铁里戴着口罩的通勤者,很难想象没了短视频、网文、游戏、音乐、网聊的慰藉,如何让一起抗击疫情的患难与共变得可以承受。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不再只是文化娱乐的代名词,它也成为民众获取衣食住行、求医问药、接受教育等民生服务的重要渠道。
但只有互联网是不够的。作为家长,你会发现,孩子在家上网课,不但“费爹费妈”,学习效果还普遍不佳。你在短视频里刷风景名胜、灯红酒绿,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云游无法取代双脚亲自去丈量好山好水。被病毒感染的恐慌,被赋黄码红码的担忧,让三年前“说走就走”的旅行变得愈发需要勇气,甚至一些必要的商旅行程也时常面临变数,包括风筝节等许多大会都改为线上召开,也都是迫不得已。
有这样感觉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我的同事王健飞,基本活在互联网上,日常都是开着至少3块屏幕工作,他还可以在车流马龙的中关村一边拿着7.8英寸的电子书阅读一边健步如飞,甚至在健身时每组动作之间的1分钟休息间隙也会拿起手机。总之,在我看来,他可以不依靠线下世界。但即便是这样的赛博朋克新物种,也感受到了难以自由旅行的痛苦。
今年8月,有一个视频号的培训项目,大概是教当地老乡如何在视频号上卖货,项目发起人找到了健飞一起参与,健飞在和我商量时,眼中透出兴奋的光。作为资深的90后互联网观察者,健飞对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有了热情,于是就有了这组封面报道中的《西南三县杂记》这篇万字长文,记录了他两次在重庆三个县市的见闻。
在他两次出差去重庆期间,通过断断续续的微信联络中,我也间接获取了许多当地的信息:重庆并非只是短视频里的五光十色的山城大都市,虽名为一市,然而地域辽阔更近似一省,三县之间多山川阻隔,山路蜿蜒,交通多费周折;当地电商并非一穷二白,而是有着不错的基础,大部分都有电商中心为当地农产品提供包装、物流服务;新消费也跟蒲公英一样在远离一线城市生根发芽,当地有各色咖啡馆奶茶店,只是美式会默认加糖,来学习的学员还组织了羽毛球协会,小城人民工作都很拼命,有的早上五点半起,晚上八九点才下班。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汇总在一起,先是搭建了项目的框架,然后录制了一档播客,接着又有了这样一篇观察笔记。确如副标题所言,这是一篇来自北京本地土著的“他者”观察。
本期封面报道的另一篇文章《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在鹤岗》来自兄弟部门“边码故事”友情供稿,他们派出了作者前往东北小城鹤岗。这几年,凭借三万一套的超低价住房,鹤岗名声鹊起,大有赶超“宇宙的尽头”铁岭之势,毕竟这里似乎是可以承载“地理套利”、安顿数字游民的理想之地。鹤岗也在我的旅行待办清单里,尽管我在B站已经刷到许多关于鹤岗的视频,但这篇文章依然提供了许多的信息增量,尤其是这里有一段百度产品经理回到鹤岗老家创业的故事,让我们有机会窥见新经济在更多城市如何生长,以及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是如何在小城里延伸。
如同城市规模一样,鹤岗这篇报道篇幅适中,随后“边码故事”组织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的对谈则扩展了这一话题的景深,毕竟学者和业者看问题的方式会不一样,作为知名的乡村研究者,吕德文也关注到了数字技术的下沉,存在于乡村生活的细枝末节,比如普通人使用的视频和购物软件;同时它也在改变乡村的业态,以及基层的治理方式;甚至,数字技术也在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脱嵌广泛发生的今天,互联网是否帮助个体“重嵌”到新的社会网络,找到一个可以依归的共同体,这些也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本期的“影像”栏目是一场接近纯粹的“在路上”之旅,作者Salome和同行人Chris,在十天里骑着他们心爱的小摩托在中国地图的东北角画了一个3200多公里的圈,期间遭遇了暴雨、大雪、甚至一度抛弃了摩托车,好在最终平安归来。这篇文章更多呈现了在路上的美好,事后的记录难免会对一路苦难不自觉美化,这也是人类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Salome在文中对《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的引用,透露了她思想深处的源头何在:“什么是好,斐德洛,什么又是不好——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答案吗?”是的,路上的美好和苦难,不应由他人来评判。
当然,那个真正改变自己人生的答案,绝不是照搬他人的教导。在路上的过程,融合了对过去的消解与对未来的建构。就像埃内斯托在23岁那年开启的南美大陆之旅,穿梭于各个国家各色人群中间,开始真切感受到社会的真相、生活的苦难,最终促使他转向对宏大命题的思考。这场旅程结束之后,那个医学生换了一个新名字——切·格瓦拉。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一场旅程中有如此顿悟,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的一句话倒是点破了更多普适的内容:“世界旅行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美好,只是在你从所有炎热和狼狈中归来之后,你忘记了所受的折磨,回忆着看见过的不可思议的景色,它才是美好的。”
在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核酸抗原自测首度显示阳性,感觉三年的这个坎儿马上要迈过去了,然后是连续四天的39度以上的高温、肌肉酸疼,如果没有早先家中留存的一盒布洛芬帮忙哄骗神经系统,整个病程的痛苦可能真的堪比一次大流感,而这期杂志的按时完成也是难以想象的。流行病学家称奥密克戎是上帝的礼物,会让感染者获得免疫力。但愿事实如此,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性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