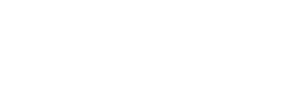为什么别人想法和我不一样

【作者简介】蒂姆·贝恩,认知哲学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意识和思维的本质、意识障碍以及能动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著有《心灵哲学导论》《认知现象》《宗教哲学》等。
【译者简介】李小霞,清华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教师。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韩非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思维是人性中的决定性特征,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然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这种能力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希腊文化的思维模式要优于其他文化的思维模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尽管希腊之外的人也能够理解别人的推理过程,但他们自己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如今,很少有人会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的思维模式优于其他人的说法,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过时: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人的思维结构从根本上讲究竟是相同的,还是像一些人经常说的那样,“他们”―—即世界“另一头”的人―—并不像“我们”这样思考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理学家往往主张普遍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讲,在所有社会中,人类的思维模式都是相同的。而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主张特殊主义,认为不同社会的思维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心理学家往往强调不同社会中的成员在思维上的共性,而人类学家往往强调他们的特性。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判断孰是孰非,远没有那么简单直接。其部分原因在于:争论中使用的术语本身就有些含糊不清。说两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不同,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的发现不同社会的思维模式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就能证明特殊主义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只要发现不同社会的思维模式可以存在差异,就能证明特殊主义是正确的?这场争论的另一个模糊之处来自经验实证: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对普通人究竟是如何思考的这一问题,其实知之甚少。绝大多数关于理性思维的心理学研究只针对美国大学生,而美国大学生这个群体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很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思维模式在所有地方都一样时,我们才有理由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普通人身上。就人类学家而言,他们研究特定文化的思维模式,可以提供详细的个案研究;但通常来讲,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把在某一文化中的研究与在另一文化中的研究进行比较。简单来讲,任何想在这场争论中分辨是非的人,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我们将集中讨论三个问题,试着厘清这场模糊的争论。第一,在思考的内容上,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到底有多大?第二,某些社会中的成员倾向于使用其他社会中的成员不使用―—也许是不能使用的推理模式吗?第三,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在这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思维争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任何对人类本性感兴趣的观察者,看一眼就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社会对于现实的看法明显不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哲学观点、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不同。考虑这个问题:非人类的动物是否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这件事显而易见,动物不能为它们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在古雅典的法律中,就有审判动物的法律条文,而且这类审判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屡见不鲜。
所以,很明显的是: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但不太明显的是,这些思维上的不同是只局限在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说这些话时我要向动物们道歉―—还是说,这些不同构成了我们思维的“核心”特征,即规范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思维特征?让我们从两个领域来考察这个问题:对空间位置的思考,以及对心智能力的思考。
对空间位置的思考,人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二是以地理方位为中心。在思考空间位置时以自我为中心,就是采用一种以自我为原点的参照系。例如,以自我为中心描述一棵树的位置,可以说,这棵树在房子的左边。(从另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看,同一棵树可能在房子的右边。)与此相反,以地理方位为中心思考空间位置时,采用的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参照系。例如,以地理方位为中心描述一棵树的位置,可以说,这棵树在房子的北面。那么,不同社会中的人思考空间位置时,使用这两种方式的偏好会有所不同吗?心理语言学家史蒂芬·莱文森(StephenLevinson)认为,确实会有所不同。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莱文森和他的同事比较了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对空间位置的思考方式。有些语言背景的人,更愿意以自我为中心描述空间位置。例如,尽管使用英语和荷兰语都能以地理方位为中心描述空间位置事实上,我在上一段话中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母语是这些语言的人非常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描述他们身处环境中物体的空间位置。相比之下,很多说其他语言的人则更愿意用地理方位做参照系。例如,说泽塔尔语―—墨西哥的一种玛雅语的人,很少(如果这么做的话)使用“左”和“右”来表述位置。说泽塔尔语的人不会让对面的人把他们左边的杯子递给自己,而是让对方把他们北边的杯子递给自己。这种在语言表述上的不同,是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对空间的思维方式不同引起的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莱文森和他的同事比较了说荷兰语的人和说泽塔尔语的人在空间推理上的不同。研究人员在桌子上向受试者展示一张卡片。卡片上有红、蓝两个点,红点在蓝点的左边/北边。然后受试者旋转180度,面对另一张桌子。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在一组卡片中找出和他们刚才看到的卡片“相同”的卡片。在这些卡片中,一张卡片具有和第一张卡片相同的自我中心位置关系,也就是红点在左,蓝点在右,但南北位置关系不对;另一张卡片具有相同的地理方位中心位置关系,也就是红点在北,蓝点在南,但左右位置关系不对。绝大多数说泽塔尔语的人选择了以地理方位为中心的角度来寻找卡片,绝大多数说荷兰语的人选择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寻找卡片。基于这些证据,以及其他不少证据,莱文森认为:语言背景习惯以地理方位为中心的人和语言背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思考空间位置的方式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然而,这种说法并非无懈可击。首先,说泽塔尔语的人和说荷兰语的人之所以做出不同选择,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实验中对“相同”这个词的解释不同。也许说泽塔尔语的人认为,研究人员让他们找出和第一张卡片地理方位关系一致的卡片;而说荷兰语的人可能认为,研究人员让他们找出和第一张卡片左右关系一致的卡片。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说泽塔尔语的人也可以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思考空间位置。心理学家佩吉·李(PeggyLi)和安娜·帕帕弗拉(AnnaPapafragou)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测试。他们向说泽塔尔语的人展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以自我为中心的推理才能解决。他们发现,受试者解决这些问题的熟练程度,与他们使用以地理方位为中心的推理解决问题的熟练程度一样。说泽塔尔语的人可能不使用“左”或者“右”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术语来说话,但他们似乎完全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
现在让我们转到人类思维的另一个核心领域:对心智能力的思考。可以说,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对心智的看法和我们对空间的看法相比,差异更大。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人们认为死者能够影响生者的思想和行为,而在当代的西方社会中,这种假设并不常见。同样,关于一个人的思想如何能影响另一个人的思想这个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能通过某些知觉渠道(比如,通过和他们说话)影响别人的思维;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认为,有些人能在没有知觉接触的情况下影响别人的思维。同样,有些文化认为,人类的知觉仅限于来自五种公认的感觉器官;而其他有些文化却认为,有的人能具有超级感官,能够“看到”和“听到”正常的知觉能力感知不到的东西。此外,在一些文化中,人们认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生病。例如,生活在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TheFederatedStatesofMicronesia)的伊法利克环礁(IfalikAtoll)上的人就认为,想念某位亲人会使那位亲人生病。
同时,有证据表明,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在思考个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时,也存在细微的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注意到,大多数人容易过分强调他们的行为受到性格特征,也就是人格的基本特征的影响,而不愿意将其归因于偶然的环境因素。比如,人们经常认为某个人在面试中紧张,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有容易紧张的倾向。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面试本就是一种不寻常的高压环境,即使最镇定的人也会感到紧张。人们总是用性格特征而不是环境因素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这种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专门有个词来形容它―—基本归因谬误。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基本归因谬误恐怕远非基本,并不能概括人类的行为。这种谬误在强调个人自主性的社会中最为明显,而在强调集体行动和遵守社会规范的文化中,这种谬误就不那么强烈―—甚至可能完全不存在。
因此,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在对心智能力的理解上的确存在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可能只是在跨文化的一致背景下的部分特例。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类在解释自己和周围人的行为时,都会诉诸信念、欲望、意图、知觉、情感、记忆以及想象力这些方面。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儿童掌握这些概念的年龄不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在哪个社会中的人,在儿童期结束时,没有全面掌握这些概念。至少,在考察了对空间位置的思考和对心智能力的思考这两点后,在物种跨文化一致性这个普遍框架下,思维中的跨文化差异虽然存在,似乎只能算是例外而已。
现在,让我们从思考的内容转向思考的模式。某个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推理模式,有可能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和另一个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推理模式完全不同吗?事实上,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某些社会的成员有没有可能根本无法掌握某些推理模式呢?在人类学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法国人类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1] 在他1910年出版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2] 一书中指出,没有文字系统的民族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这种社会中的成员“没有能力进行最低程度的抽象推理”。20世纪30年代,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3]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验证。他考察了乌兹别克斯坦一群目不识丁的农民,看看他们能否掌握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一组研究中,他告诉农民,在极北地区,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而北冰洋内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属于极北地区。然后他问这些农民,新地岛上的熊是什么颜色?只有不到30%的农民做出了正确的推理。有些农民回答说,他们不知道熊的颜色。据记录,其中有个农民说:“你见过它们,所以你知道;但我没见过它们,我怎么知道?”相比之下,在同一个社会中,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就可以轻易解决鲁利亚提出的推理问题。
鲁利亚由此得出结论,不识字的农民缺乏推理能力。而且,他把这个结论推而广之,认为一个人需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掌握抽象推理能力。现在,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正规教育促进了一个人的抽象推理能力,但鲁利亚的研究是否表明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就不能进行抽象推理,这一点还不清楚。
在考虑鲁利亚的实验结果时,要记住两点。首先,意识层面的思维十分消耗体力,使人疲劳,特别是在思考一个不熟悉的话题时更是如此。鲁利亚提问的那些农民之所以对那些问题回答得那么糟糕,也许与他们的理解能力有关,但更可能与他们的动机水平有关―—他们看不到费劲思考和回答这些和他们的生活没有明显关系的问题有什么好处。其次,正如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Lloyd)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之所以提出问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鉴于此,人们可能会想,那些农民是不是在听到鲁利亚提出的问题(“新地岛上的熊是什么颜色?”)后,认为鲁利亚对极北地区熊的颜色的确一无所知,进而怀疑到“在极北地区,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这句断言―—这句话在形式上看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毕竟难以验证。事实上,农民们可能担心,如果他们这么轻易就接受鲁利亚的主张,会让人觉得他们好糊弄。毕竟,他们自己并没有到过极北地区,而鲁利亚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他们凭什么问都不问就信以为真呢?近年来,对于没有文字的社会,人们在研究其社会成员的推理思维能力时,也考虑到了上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转变做法,要求受试者通过推理,想象在一个虚拟星球上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发现,以这种方式提问,受试者的表现会好得多。这说明,他们在“非假设性”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可以归因于上述那些实用主义因素。而且,这些表现并没有说明他们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缺乏“抽象”或者“脱离实际环境”思考的能力。
近年来,关于推理模式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争论,重点已经不是在有文字的社会和没有文字的社会之间的对比了,而是在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对比上。多年来,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Nisbett)和他的合作者一直认为,东亚人(日本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尼斯贝特和他的同事指出,东亚人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西方人倾向于从分析的角度进行思考。这种观点―—东亚人是整体型思维,而西方人是分析型思维―—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尼斯贝特和他的同事认为,面对问题时,东亚人往往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而西方人往往集中考虑问题的关键要素;在面对诸多事物时,东亚人往往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将它们归类,而西方人往往根据事物的共同属性将它们归类;在推理思维中,东亚人往往基于相似度进行推理,而西方人往往基于规则进行推理。
尼斯贝特和他的合作者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这些主张。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展示了八段彩色动画。每张图片都包含一些吸引目光的物体―—或体积较大,或色彩亮丽,或是快速游动的鱼;同时也包括一些不吸引目光的背景物体,比如岩石、气泡和缓慢移动的动物。在让受试者观看这些图片一段时间后,他们要求受试者说出都看到了什么。尽管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提及鱼的次数相同,但日本学生提及背景物体的次数是美国学生的两倍。此外,当日本学生开始描述图片时,他们通常从整来描述看到的场景―—“它看起来像一个池塘”;而当美国学生描述图片时,他们通常从吸引目光的物体开始说起:“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鳟鱼,游到了左边。”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大学生看三个一组的单词,比如“panda”(熊猫)、“monkey”(猴子)以及“banana”(香蕉),然后问他们这三个单词中哪两个关系最密切。一般来说,美国学生会把“熊猫”和“猴子”分在一组,表明他们更喜欢按对象的共同属性把它们分成一类;而东亚学生更愿意把“猴子”和“香蕉”分在一起,表明他们更喜欢按对象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分成一类。
第三项研究考察了东亚学生和美国学生是如何进行归纳思维的。受试的学生面前有一张屏幕,屏幕底部展示一个目标物体,顶部则有两组物体。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学生说出,目标物体与哪一组物体更“相似”,或者更“属于”哪一组。
可以用两种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采用“家族相似性”的方法,受试者可以将目标物体归类到左边的一组花里,因为总的来说,目标物体与这些花最像。如果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受试者可以将目标物体归类到右边的一组花里,因为目标物体与这些花有一个共同属性:它们的花茎是直的。大多数东亚学生都是按照“家族相似性”来为目标物体分类的,而大多数欧美学生都是基于“规则”对目标物体分类的。(有趣的是,亚裔美国学生的表现介于东亚学生和欧洲裔美国学生之间。)
这些研究当然值得重视,但它们是否真如尼斯贝特所言,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推理方式上存在本质区别”呢?我们有理由对此持谨慎态度。
首先,“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不同,只在对比群体表现时才会体现出来。许多东亚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典型的美国学生一样,反之亦然。其次,个体是不是采用整体型思维,采用的程度有多高,在各种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很小。换句话说,很多人在某些情况下会采用整体型推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然。这表明,区分这两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再次,这些研究针对的对象都是大学生,而大学生的思考方式可能并不能代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思考方式。最后,就东亚学生与美国学生在推理方式的不同而言,这些不同看上去并不是固定的,而且很容易发生逆转。美国学生随时会把“猴子”和“香蕉”配对,而东亚学生也随时会把“猴子”和“熊猫”配对;东亚学生可以按照指示基于“规则”进行分类,美国学生也可以按照指示根据“家族相似性”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即使东亚人和西方人在采用认知策略的优先级上不同,但他们似乎都拥有同样的推理策略可供选择。显而易见,正如本章开头题词中引用的那段话一样,分析论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一点儿都不罕见。
特殊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之间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像许多理论家主张的那样―—是语言塑造了思维结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不同文化间的思维模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所讲的语言明显不同。但是,语言真的塑造了思维结构吗?
在关于思维本质的众多争议中,这个问题也许争议最大。尽管人们普遍承认,掌握一种自然语言对思维模式具有变革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指出的那样),但对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否影响、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思维结构,人们却没有普遍的共识。一些理论家认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另一些人认为就思维模式而言,语言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就像许多争论一样,真相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主张语言的结构特征对于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说法被称为“沃尔夫假说”[4]。它是以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Whorf)的名字命名的,他在20世纪中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说。但直到最近,“沃尔夫假说”才逐渐在认知科学领域中得到了普遍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布伦特·柏林(BrentBerlin)和保罗·凯(PaulKay)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项关于色彩感知差异的跨文化研究。柏林和凯发现,尽管不同语言中描述色彩的词语数量不同,但关于色彩词语的结构方面,在不同文化中似乎都一样。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词语描述颜色,那么这两个词语就是黑色和白色;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三个词语描述颜色,那么第三个词语总是红色;如果一种语言有三个以上的词语描述颜色,那么多出来的词语将会是绿色、蓝色或者黄色。这表明,如果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之间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那也是思维结构在影响语言结构,而不是相反。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发现表明思维是独立于语言的,但现在看来,下这个结论可能为时过早。首先,最新的证据表明,色彩感知可能并非完全不受语言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说俄语的人比说英语的人对浅蓝和深蓝的感知更强烈。在俄语中,浅蓝和深蓝是用不同的词语表达的;而在英语中,这两种颜色都用蓝色表达,只是明暗程度不同。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因为语言对色彩感知没有影响,就认为语言对思维结构没有影响,这显然是不对的。毕竟,如果语言真的对思维结构有什么影响,那么从先天的角度看,这些影响更有可能发生在不稳定的、最新进化出来的心智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稳定的、古老的心智过程中。
也许我们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否认“沃尔夫假说”,但我们能找出什么好的理由相信它呢?在一项关于中英文双语使用者对刻板印象的表征研究中,人们发现了一些迹象,说明语言结构塑造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结构。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来描述一些人格特征。其中有些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表达(比如“artistic”“liberal”),但无法对应翻译成一个中文单词;另一些可以用一个中文单词表达,但无法对应翻译成一个英文单词。然后,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只阅读英文描述,另一组只阅读中文描述。五天后,研究人员就受试者读到的人格描述内容,来询问他们一些问题。结果显示,对于可以用一个单词描述的人格特征,受试者记得更牢,做出的推论也更多。换句话说,他们阅读的人格描述是由哪种语言写成的,对于激活哪种刻板印象是有影响的。
关于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数学认知领域的研究。其中一组研究探讨了一种语言中的数字词语对于儿童获得数学能力的速度是否有影响。有人认为,比起说中文的儿童,说英语的儿童学习从10数到20更困难。这是因为在中文里,这段数字的发音和英语相比更有规律[例如,11(eleven)在中文里读作“十一”]。其他研究发现,在同时说威尔士语和英语的儿童中,他们用英语做计算时的水平比用威尔士语做计算时高。这一发现也许可以解释为,威尔士语中的数字词语比英语中的数字词语长。
但语言对数学思维最深远的影响,也许在于数学词语的丰富程度。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指出的那样,许多非人类物种可以用近似的方式表征数学关系;因此,在数学词语贫乏的社会中也存在这种能力,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似乎没有能力准确地思考数字关系。对亚马孙流域的毗拉哈语(Pirahã)和蒙杜鲁库语(Munduruk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在蒙杜鲁库语中,没有表示5以上整数的词语,而在毗拉哈语中,甚至没有表示数字1或者2的词语。在这些语言中缺乏数字词语,使得这些人对数学关系的把握出奇地差。例如,说蒙杜鲁库语的人似乎无法分辨从6个物品中减去4个,是会剩下2个物品、1个物品,还是什么都不剩。虽然这里的数据还有些模糊,但这项研究表明,以精确的方式进行数学关系推理,恐怕需要掌握数字词语。
上面这些论述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从根本上讲,人类的思维模式到底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相同的(如普遍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还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思维的本质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如特殊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呢?
一方面,答案取决于一个人的视角。当我们考虑自己的基本认知能力时,比如判断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根据事物之间的关系或共有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普遍主义的解释似乎是最合理的。虽然有证据表明,不同社会的成员有可能更愿意使用某种推理模式,但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成员所使用的推理模式超出了另一个社会成员的理解范围。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同社会成员的思考范围是不同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社会中的数字词汇对于其成员的数学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词汇并不是扩展思维范围的唯一工具,因为人类的思维是通过多种方式构筑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受到所传承的文化习惯的影响。比如用手指来归类和数数,或者要一次记下许多事情时,有人会想象把它们依次放在自己家中的房间里。思维模式会受到社会体系的限制,比如学校、科学团体和出版社;思维模式还受到各种人工制品的限制,比如六分仪、计算尺和智能手机。因此,即使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是一致的,但一个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可能和另一个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相差很大。因为对认知领域的把握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基本认知能力,还取决于这些能力的构筑方式,而这些思维模式的构筑方式,在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为什么只有人类会思考?》
作者:[澳]蒂姆·贝恩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 出品方:读客文化
原作名:Though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译者:李小霞 | 出版年:2022-2-1
页数:184 | 定价:36.00元
装帧:平装 | ISBN:9787571112271
[2] 《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LesFonctionsMentalesdanslesSociétésInférieures)
[3] 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RomanovichLuria,1902—1977),苏联心理学家、内科医生,神经心理学的创始人。
[4] “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又称为“语言相对论”,是关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