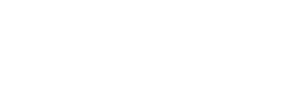经营与行善,蛋糕经济学可以兼得吗?

【作者简介】亚历克斯·爱德蒙斯(Alex Edmans)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公司治理中心学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经济学等。他是顶级学术金融期刊《金融评论》(Review of Finance)的主编,其研究常被《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彭博社、路透社等媒体刊登。他被Poets & Quants评为年度教授,因推动金融界的变革而获得未来金融奖,并登上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雷达榜单(Thinkers50 Radar)。
虽然蛋糕经济学作为一个概念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免显得太过美好,有些虚幻。要是一家企业真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创造利润这一副产品,那它就太实用了。但许多企业似乎都忽视了利益相关者这样的事实就是在暗示蛋糕经济学在实践中并不奏效。就算蛋糕可以做大,但说不定需要太多投资,导致利润下降,下图可能是规律,而不是例外。
第默克公司的故事,看起来像是支持蛋糕经济学的例子,其实并不一定。我完全可能研究过上万家企业,从中选出一个做大了蛋糕又赚到了钱的最合适的例子。对任何观点,你都能找到故事来加以支持。如果默克公司并未发起异阿凡曼菌素捐赠计划,它说不定更赚钱。
所以,我们还是看看证据吧(贯穿本书,我会时不时地喊出这句咒语)。做大蛋糕最终会让投资者受益吗?换句话说,利益相关者价值(也叫“社会绩效”)是否会提高股东价值(也叫“财务绩效”)?这就是我们将在本文中探讨的主题,我们将运用来自多个学科的严谨研究——不仅是金融和经济学,还包括战略学、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和会计学。任何研究的出发点都要先确定怎样衡量社会绩效。社会中包含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所以你通常会选择聚焦到一种利益相关者身上,比如说环境。接着,你可以选择绩效的输入指标(企业在环保倡议上花费了多少,或者企业是否有节能政策)或输出指标(企业减少了多少能源消耗,或者外部机构对其环保记录的评估)。再接下来,是确定怎样衡量财务绩效——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最后,你计算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这一相关性非常重要,已经有数百项研究对此做了调查。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你要怎么找出整体共识呢?这里要用到的是元分析,它是指“对研究展开研究”,汇集各项研究的结果。约书亚·马戈利斯(Joshua Margolis)和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分析了1972年至2002年间的127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企业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正相关,当然,很少有负相关的证据。”马克·奥里茨基(Marc Orlitzky)、弗兰克·施密特(Frank Schmidt)和萨拉·莱恩斯(Sara Rynes)进行的一项独立元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但这些元分析涵盖的研究只记录了相关性,并未记录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高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可能导致社会绩效,因为高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使企业能够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投资。或者,还有一些变量遭到了忽视——是第三个因素(如良好的管理)共同改善了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除了相关性和因果性,还有其他许多考量:
① 一些研究使用了可疑的社会绩效衡量指标。早期的研究会直接询问管理层对某一种利益相关者有多么关心,但管理者哪怕并不关心,也会说自己关心。另一些研究使用了企业自己披露的信息,但它们可以假装善良,哪怕它们实际上并不——这种做法,叫作“漂绿”。还有一些研究使用了输入指标,也即为利益相关者支出了多少,但这难以说明此类支出能带来多少输出,光是花钱并不能做大蛋糕。
② 一些研究使用了可疑的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市场份额、收入和利润全都未将风险考虑在内。聚焦于利益相关者资本的策略存在风险,因为如果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它无法利用自己的环保记录来筹集资金。投资者在乎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求股票投资比银行储蓄获得更高的回报。
③ 一些研究着眼于短期,因此可能靠的是运气——这就好比,一个主张投资债券的人说,1999年至2009年债券表现优于股票。这的确不假,但通常情况下,股票表现是优于债券的。
④ 一些研究只考察了单一行业,并不清楚这些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行业。
由于社会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尚无定论,我决定自己研究一下。我首先要决定的是怎样衡量社会绩效。我选择了员工满意度(也即一家企业怎样对待员工),因为这方面存在一个特别好的产出衡量指标,那就是美国100家最值得效力的企业名单,由加利福尼亚州最佳职场研究所(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评选,1998年开始每年在《财富》杂志上公布。这份榜单是最彻底的分析。它调查了250名各级员工,向他们提出57个问题,涉及诚信、公平、尊重、自豪和同事情谊。最佳企业分布在不同行业——1998年,最具代表性的行业是金融服务(服务业)、消费品(低技术制造业)和制药(高科技制造业)。
这份榜单从1984年开始就可以查阅到,当时以独立发行的形式公布,后于1993年更新,最后才交由《财富》杂志代为公布。故此,我最初的研究覆盖到2009年,共有26年的数据;后来,我又把它延长到2011年。其间包括两次大规模经济衰退: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由于ESG投资近年来才成为主流,其他大多数衡量社会绩效的产出指标也都是直到21世纪头10年才出现——而同期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因此,说社会绩效在21世纪头10年改善了财务绩效恐怕难以叫人信服,因为它或许暗示蛋糕经济学只有在经济上升期才能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处境艰难,企业兴许需要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
(1)
数据挖掘与伪相关
研究员工满意度还有第二个原因——有关它为什么可转化为财务绩效是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的。在许多现代企业中,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企业依靠员工赢得客户关系,研发新产品。更高的员工满意度,可以让企业招到和留住最优秀的员工,让他们更有动力,生产力更强。社会绩效的其他维度与财务绩效的联系就不那么清晰了,尤其是在不满足实质性原则的情况下。例如,在许多行业中,动物权利恐怕并不重要。
我们之所以期待社会绩效转化为财务绩效存在明晰的联系,在逻辑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要避免数据挖掘问题。发现一项揭示了重大结果的研究能带来很大的回报。如果教授发现一个变量能预测股票回报率,那么,他有很大的概率发表新论文。如果一家新成立的共同基金在发行说明书中宣称满足了该变量,便能吸引到投资者。故此,人们有动机去挖掘数据,进行上百次回归分析,将股票绩效与大量变量关联起来,努力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其中一些变量兴许是合理的,比如首席执行官的奖金或教育程度。但如果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变量,哪怕是对它们进行100次回归分析,比如首席执行官的鞋子码数、姓氏中的字母数量或最喜欢的颜色,总会有5次回归分析纯属偶然地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这种偶然结果叫作伪相关性。你可能会发现喜欢红色的首席执行官表现更好——这是一种伪相关性,因为喜欢红色就能提高绩效是没有原因的。可一旦揭示出了关系,你总是可以编造故事来加以解释。你可以挖掘心理学文献,找到一项研究声称红色能激发支配能力,进而提高绩效——事实上,罗素·希尔(Russell Hill)和罗伯特·巴顿(Robert Barton)的确做过这样的研究。还有可能,你发现喜欢红色的首席执行官表现更差,你会搜索相关研究,表明红色与失败的风险相关,并导致恐惧——这样的研究也存在,是由安德鲁·埃利奥特(Andrew Elliot)、马库斯·迈尔(Markus Maier)、阿伦·莫勒(Arlen Moller)和约尔格·迈因哈特(Jorg Meinhardt)进行的。一些伪相关性已经出了名,比如“超级碗效应”。该效应指的是,如果美国橄榄球联合会(AFC)的一支球队赢得了超级碗,市场往往会下跌;如果赢得超级碗的是国家橄榄球联合会(NFC)的一支球队,市场就会上涨。一些顾问甚至建议利用这一效应进行投资。但超级碗冠军何以会影响股市,完全找不到理由。在当今的“大数据”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数据来源,计算能力也没有极限,挖掘数据的能力尤其令人担忧。金融学教授罗伯特·诺维马克斯(Robert Novy Marx)便戏仿这种能力,利用曼哈顿的天气、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的温度异常)、太阳黑子和行星的排列来预测交易策略的表现。他诙谐地说:“其他人似乎可以复制我的成功,尤其是考虑到……候选解释变量能很便利地获得、机器可读的候选解释变量数据呈指数增长,以及运行这类回归特别容易。”
因此,在查看数据之前,必须选择一种与财务绩效存在合理关联性的社会绩效衡量指标,这可以降低伪相关性的出现概率。
决定好怎样衡量社会绩效后,我接下来要决定的是怎样衡量财务绩效。此前的研究着眼于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它们会遇到如前所述的因果关系问题。所以,我研究的是未来的股票回报率。这很有帮助,因为股票回报率指的是股票价格从当前到明年的变化(加上股息)。要使股票回报率高,不光需要明年的股价高,还需要当前的股价低。股市在考虑财务绩效方面做得相当好——事实上,一种普遍的批评是,它过分关注财务绩效。如果公司当前的股价很低,这可能意味着当前的财务绩效也低。
那么,这怎么让我们更接近因果关系呢?假设虚构的企业“超级超市”出现在今年的最佳企业榜单上,再假设这是一个员工满意度高会带来未来更高财务绩效的世界。超级超市当前的财务绩效并不突出,所以股价仅为100。接下来的一年里,动力十足的员工们提高了公司的利润,将股价推高至120。假设市场回报率只有7%,而超级超市的股票回报率是20%,那么,它战胜了市场。
现在再来假设一个因果关系反过来的世界——员工满意度仅仅是本就强劲的财务绩效带来的结果。由于超级超市利润高,当前它的股价就已达到112,那么,股价涨到120的回报率是7%,和市场没什么区别。因此,只有当员工满意度提高了财务绩效,而非反过来时(财务绩效提高了员工满意度),最佳企业才会打败市场。
因此,关注未来的股票回报可以减少因果关系颠倒问题,但此时仍然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超级超市的股票回报率达到20%,也可能是由于许多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动力十足的员工。兴许,整个超市行业绩效都很好。兴许,超级超市是一家小企业,有证据表明,小型股往往强于大型股。有可能,该企业近来绩效都很好,只是市场对此认识迟钝。还有可能,我认为市场长于整合利润的假设做得太草率——也许超级超市的股价当前就应该是112,但市场错了,只给出了100。
为分离出员工满意度的影响,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我不光研究了超级超市,还研究了上市的每一家最佳企业。如果超级超市打败了市场,可能是因为它规模较小或近期绩效强劲。但如果许多家最佳企业(有着不同的规模、有着不同的近期绩效、来自不同的行业)都跑赢了市场,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员工满意度。
其次,我控制了遗漏变量。只有当最佳企业分布在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规模、过往绩效不同的时候,研究它们的做法才奏效。但如果很多最佳企业都是科技公司,而科技行业本身就击败了市场,那么,哪怕员工满意度是个不相干的因素,最佳企业同样表现出色。
因此,我不光将超级超市与整个股市进行了比较,还比较了超市行业的其他企业,或其他近期绩效良好的小企业。我对每一家最佳企业也都做了同样的比较。如果最近绩效不佳的大企业“自动汽车公司”也在名单当中,我就把它与其他汽车企业或其他近期绩效不佳的大企业进行比较。因此,每一家企业都有了专门定制的对照组。除了行业、规模和近期绩效外,我还控制了其他几个因素,如股息、当前估值和股票交易量。重要的是,我还可以控制风险。目前还没有既定的方法来根据风险调整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但数十年的金融研究已经提出了调整股票回报的工具。最著名的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我使用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叫作卡尔哈特模型(Carhart model)。
我用了4年时间完成这项研究,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并排除了其他解释——包括这里没有考虑的另外几种解释。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研究了1682个公司财年之后,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我发现,在28年的时间里,美国最值得效力的100家企业的股票回报率平均每年超过同行2.3%~3.8%。这累积起来是89%~184%。
(2)
幅度可信吗
研究人员通常都想要发现重大结果,因为这会让他们的研究结论更引人注目。每年2.3%~3.8%,持续28年,这是不容小觑的数字。如果一位基金经理连续5年超过市场表现2%,人们就会认为他技术高超。故此,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实现了更高的绩效,显然很扎眼。
但我们还必须检查这些结果是否太大以致失去了可信性。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有一种交易策略每年都超过市场20%,任何投资者都会惊讶得咖啡杯掉到地上,而且推特上人们会铺天盖地地转发这种策略。尽管有理由相信有些交易策略每年能产生2.3%~3.8%的超额回报,但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段之内,你不太可能每年超过市场表现20%。该研究可能只考虑了很短的时间段,或并未控制其他因素。如果一种商业实践真的让一家企业每年超过同行20%,那么,凡是不采用这种实践的企业,很快就会被逐出市场。很少有人做过这种诉诸现实世界的理智核查。大多数人都明白,对于那些看起来“好得难以置信”的交易——特价旅游、汽车或电视机——需要谨慎对待。但对于证据,人们往往欠缺同样的谨慎态度。研究结果越惊人(声称能带来极高回报的交易策略或商业实践,或是说能减掉多少磅的减肥药),就越能吸引注意力。尽管赚钱和减重的机会的确存在,但每年赚20%或一夜之间治愈肥胖症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你兴许好奇为什么我花了4年时间才发表论文,而媒体、咨询公司和投资机构随时都在发布说明商业实践或交易策略回报情况的研究。这是因为,我经受了严格的同行审阅,使得这篇论文在严谨程度上远远超过单靠我一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地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主要借鉴的是顶级学术期刊所发表的研究。
我寄去的论文被第一份期刊拒绝了,相关人员说我的研究结果“有趣但令人费解”。编辑和同行审阅人员都不相信市场是低效的,也不相信会产生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策略。哪怕你能打败市场,他们也很怀疑员工满意度这样缥缈的东西是否靠得住。因此,我必须更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员工满意度可能会提升企业价值,而不是浪费开支。我必须澄清为什么哪怕员工满意度有价值,也可能遭到市场忽视。
一旦遭到期刊拒稿,你就没法把这篇论文再寄给同一刊物了。于是,我又把它提交给了第二份期刊,但也遭到了拒绝。当时,我只研究了截至199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佳企业榜单。副主编担心,数据的时间跨度太小,无法得出概括性结论,尤其是同一时期还包含了互联网泡沫。而且,他还担心,我的结果可能是由少数表现异常的个股推动的,这些个股使得“最佳企业”投资组合整体表现优于市场,哪怕大多数个股表现不佳。同行审阅人员还说,我需要查明员工满意度高会带来更高股票回报的机制——是什么导致最佳企业的股价上涨?有可能员工满意度实际上并没有价值,但市场错误地认为它有价值,因此对员工友好型企业会给出更高的估值。
所以,我又重新开始,查阅了1984年和1993年以图书形式发布的名单,将研究追溯到1984年,并针对副主编的担忧,消除了异常值的影响。为了提供关于这一机制的进一步证据,我研究了最佳企业的未来利润——如果员工满意度改善了招聘、留任和激励,这应该能提升绩效底线。但仅仅研究利润还不够。如果一家最佳企业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但股市已经预期到这一点,股价应该就不会变动。因此,我将最佳企业的季度利润与高盛、瑞士信贷等机构股票分析师事先预测的利润进行了比较。我发现,最佳企业系统性地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也叫“盈利超出预测”),导致它们的股价大幅上涨。事实上,2.3%~3.8%的年涨幅中,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财报发布日。
我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只有三份金融期刊被视为顶级期刊,可凭借在它们上面发表的研究,在沃顿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第三份期刊的同行审阅人员也有很多担忧,但他至少没有径直拒绝,而是给了我“修改并重新提交”论文的机会,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让他相信,这种战胜市场的幅度是可信的(参见“幅度可信吗”专栏),并反驳股票回报率上升的其他三种解释:第一种,社会责任基金购买了最佳企业的股票,因为它们将员工满意度作为选股标准,而它们的购买推高了股价。第二种,员工满意度高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正是后者带来了较高的回报。第三种,员工满意度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无关紧要,但市场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并按折扣价对最佳企业做了估值,较高的后续回报只是把折扣又添补了回来。
我解决了这些问题,对论文做了重大修改,并给同行审阅人员写了一封长达17页的信,解释自己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但他仍然不满意,并要求再次修改。我需要将一直留在榜单上的企业与后来新增或除名的企业进行比较,以确保结果并不主要受1984年的最初榜单所推动。如果近年来的榜单主要受原始榜单所推动,那么,结果可能不光不具备普遍性,还很令人费解:为什么最佳企业榜单上的企业20年后仍能产生更高的回报?我还得研究最佳企业的优异绩效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话题我稍后会再讨论。除了所有审阅人员的具体担忧,由于距离我最初撰写这篇论文已经过去了4年,所以我必须更新最近这4年的数据,保证结果仍然有效。
终于,论文通过了。

经受了持怀疑态度的编辑和同行审阅人员这么多年有凭有据的考问,我终于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善待员工的企业绩效也很好。这看似有点缺乏冲击力。快乐的员工比不快乐的员工更有效率,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真的有必要浪费4年时间来揭示一些人们凭常识就能猜到的事情吗?
事实上,这一结果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显而易见。以好市多超市为例。2014年,好市多给员工的工资是每小时20美元,几乎是美国零售业员工平均工资(11.39美元)的两倍。它为其中90%的人提供医疗保险——部分原因是兼职员工在入职6个月后就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而在其竞争对手沃尔玛工作则需要2年。好市多在美国所有的主要公共假日都闭店不营业,哪怕这些日子的营业利润特别高(因为顾客不用上班,有时间出门购物)。但好市多关闭门店,让员工也能与家人一起放假休息。所有这些政策导致的成本很高,甚至把一些股票分析师和投资者逼到发狂。《商业周刊》援引一位股票分析师的牢骚:“(好市多的)管理层专注于……员工,损害了股东利益。在我看来,我干吗要买它的股票呢?”还有人抱怨说,“分给员工的东西,都是从股东口袋里掏出来的”。
这就是分蛋糕思维。它假设好市多能产生的价值量是固定的,故此,多分给员工的部分必然是牺牲了投资者的部分。《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也表达了这种思维:《好市多困境:是善待员工,还是善待华尔街》。关键词为:“是……还是……”
但蛋糕大小不是固定的。以工资、医疗保险或假期的形式分给员工的每1美元,都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士气,增大他们留下来的可能性。于是,员工可能会付出2美元的劳动把蛋糕做大,因此,投资者获得了收益,并不是损失了1美元。好市多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在同一期《华尔街日报》上说:“从第一天起,我们经营企业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薪酬高于平均水平,提供一份能维持生活的薪酬,拥有积极的环境和良好的福利,我们就能够聘用到更好的员工,他们也会在企业工作得更久,工作效率也更高。”事实上,组织行为学学者英格丽德·史密斯·富勒默(Ingrid Smithey Fulmer)、巴里·格哈特(Barry Gerhart)和金伯利·斯科特(Kimberley Scott)发现,在最佳企业工作的员工的确更乐意留下来。在我着手研究前后,好市多的员工流动率是17%(入职一年后即降到6%),相比之下,沃尔玛为44%。由于更换一名员工的成本大约是其年薪的1.5~2.5倍,故此,减少人员流动成本对股东来说是件好事。正如好市多的首席执行官吉姆·辛内加尔(Jim Sinegal)所说,“我们的薪酬比沃尔玛高得多。这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一桩划算的生意”。
说到生产力和士气,组织经济学家丹尼尔·西蒙(Daniel Simon)和杰德·德瓦罗(Jed DeVaro)发现,客户满意度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干劲足的员工会设计出更好的产品,在与客户的互动中更加主动积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发现,不管是在制造业、服务业、高科技行业还是在低技术行业,成为一家最佳企业都能带来类似的回报。起初,我认为员工满意度在苹果这样的公司更重要,因为它们的员工通过创新,会对公司绩效造成显著影响。然而,在诸如零售业等行业,员工同样是实现积极客户体验的关键,同样有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把“是……还是……”变成“既……也……”将员工视为企业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或一种需要最小化的成本,这对员工和华尔街都有好处。做大蛋糕并非不可能之事——投资员工,也是在为投资者考虑。
我的研究表明,善待员工从长远来看会让投资者受益,但这项研究并未讨论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会受影响。幸运的是,有一些研究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加以检验。市场研究人员克莱斯·福内尔(Claes Fornell)、苏尼尔·米萨斯(Sunil Mithas)、福里斯特·摩根森(Forrest Morgeson)和M.S.克里希南(M. S. Krishnan)调查了客户满意度和股票回报之间的联系。1997年至2003年间,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排名前20%的企业获得的回报几乎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两倍。同样,这个结果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提供更低的价格、更量身定制的产品和免费的售后服务,客户满意度会提高,但这些措施可能会降低利润。事实上,现在让我们把前述《商业周刊》上股票分析师的牢骚补充完整。该分析师的完整抱怨是,“(好市多的)管理层专注于客户和员工,损害了股东利益”。
在环境方面,创新投资战略价值咨询公司(Innovest Strategic Value Advisors)推出了一项“生态效率”指标,用于表示一家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与其产生的废料之比。杰伦·德瓦尔(Jeroen Derwall)、纳迪亚·京斯特(Nadja Guenster)、罗伯·鲍尔(Rob Bauer)和谢斯·考迪克(Kees Koedijk)发现,1995年至2003年间,该指标排名靠前的股票每年比排名靠后的股票高出5%。
还有一种方法不是聚焦于某个利益相关者群体,而是将覆盖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绩效进行汇总。KLD是一家顶尖的ESG数据供应商(现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所有),根据51个利益相关者问题对企业进行打分,这些问题涉及7个主题:社区、治理、多样性、员工关系、产品、环境和人权。会计教授莫扎法·汗(Mozaffar Khan)、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和亚伦·尹(Aaron Yoon)研究了1992年至2013年间的2396家企业。他们发现,在ESG方面得分高的企业,绩效仅比市场高出1.5%,在统计上不显著(换句话说,这个幅度太小,可能纯属偶然)。这项研究似乎并未有力地支持蛋糕经济学。
但这里有个转折。回想一下实质性原则,只有向具有实质性的利益相关者交付价值,最终才会使投资者受益。上述研究者根据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设计的实质性导图,根据每家企业所在的行业,将这51个问题分为实质性问题和非实质性问题。在实质性问题上得分高的企业,绩效比市场高出4.83%。因此,对一家企业来说,只在少数几项上做得好,并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克制,实际上比全面做得好更好。不加区分地投资于利益相关者不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价值,但有针对性地投资于实质性利益相关者则可以。
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上面的结果。一些投资者用打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评估。如果一只股票获得的肯定多,满足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它将被视为更好的投资。但如果一只股票优先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那么,它可能就不会更优先考虑股东。想为所有人做所有事,一家企业最终可能变得对任何人都不值一提。
上述所有研究针对的都是股东回报,而迈克尔·哈林(Michael Halling)、余锦(Jin Yu)和约瑟夫·策希纳(Josef Zechner)则针对企业的债务利率做了调查。人们普遍认为,负责任的好处是,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筹集资金,这可能是因为,在人们眼里,心怀宗旨的企业是更稳妥的投资对象。虽然你无法观察到股东在投资一家企业时期望获得多高的回报,但你可以观察到债券持有人在这方面的期待——因为这一期待跟他们收取的利率相符。这三名研究者发现,更高的整体社会绩效拉低了利率,这似乎是负责任企业的一场漂亮仗。
但深入挖掘后,他们发现,与产品相关的维度才是最重要的。环境、社区和人权得分其实反而与更高的利率有关,尽管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业的变化,能对绩效产生积极作用的特征会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关系在经济衰退期间失去显著性。但在工人稀缺的繁荣期,良好的员工关系确实会降低利率——或许是因为这有助于留住员工和开展招聘。从行业来看,在农业、林业、渔业和采矿业(环境在这些行业可能有着实质性意义),环境得分和低利率相关。但在交通、通信和贸易领域,社区得分高反而会提高利率,这或许暗示企业把焦点放到了不重要的问题上。
请注意,最后两项研究并不意味着企业应该只聚焦于具有高业务实质性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永远都可以选择优先考虑对自己有着内在实质性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研究仅仅表明,这样做或许不会提高长期回报。如果股东愿意牺牲长期回报来追求社会目标,这没问题——股东福祉不仅仅包含股东价值。然而,领导者和投资者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种权衡取舍——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社会绩效总能提高财务绩效。
还有一种方法考察的不是对利益相关者投入进行投资所实现的产出,而是着眼于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政策的使用情况,这是一种投入指标。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支持员工技能培训、提高用水效率或根据人权标准选择供应商的政策。鲍勃·埃克尔斯(Bob Eccles)、扬尼斯·约安努(Ioannis Ioannou)和乔治·塞拉费姆(George Serafeim)精研了企业的年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采访了200多名高管,调查企业是否真的采纳了相关政策(而不是单纯地宣布有这方面的意图)。1992年之前就采取了政策的企业,在1993年到2010年间,比那些说到没做到的企业业绩要好2.2%~4.5%。引人注目的是,在1992年,负责任的企业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哪怕10年后,也只有十来家《财富》500强企业发布过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不会因为来自监管机构、投资者或公众的压力而被迫采取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政策。相反,它们这么做是出于自愿,因为它们希望自己的业务能为社会服务。
这一观察很重要。目前,负责任的企业在一些国家仍处于萌芽状态——当地投资者忽视社会绩效,也少有公众监督。这些国家的情况跟1992年的美国类似。因此,那些特别具有前瞻性,并自愿持有“做大蛋糕”思维的企业,可能成为未来的赢家。由于大多数企业不关注社会价值,故此,关注社会价值的企业应该享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掌握了这些证据,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企业应该追求利润还是社会价值的讨论。确实存在一些不太可能反映在利润上的真正的外部性。但研究结果表明,真正的外部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企业一般认为的外部性长期而言实际上会影响利润。综上所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实现利润,要沿着宗旨的道路走下去。
上述研究的第一点含义是,一家企业的成功跟它向利益相关者交付的价值有关。因此,服务社会是首席执行官级管理层应该重视的问题,它是企业怎样经营的基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任务,可以交给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
第二点含义更发人深省,而且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做大蛋糕对投资者有利,但仅限于长期。这些研究使用的所有指标都来自公开信息。例如,拥有近2000万线下和线上读者的《财富》杂志,每年的2月刊都会大张旗鼓地发布“最佳企业”榜单。如果股市有效(也即,如果它能很好地将信息纳入考量),那么,《财富》杂志2月刊在1月中旬刚一出现在报刊售卖点,所有最佳企业的股价都应立刻猛涨。等到2月1日我开始计算股票回报率的时候,股价应该已经很高了,那么,在此之后,最佳企业的表现不应继续优于市场。故此,研究暗示,市场并未对榜单做出充分回应。
而且,市场的低迷不仅仅持续两个星期(从1月中旬到2月1日)。我发现,它持续了4年多。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表明,只有当最佳企业公布更高的季度收益时,市场才开始注意到该企业。结果还表明,即使是专业的股票分析师也没有意识到员工满意度会提高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低估最佳企业的收益。
这一结果揭示了股市对什么进行估值、不对什么进行估值。市场并不直接对诸多无形资产进行估值,而是等它们日后显现出有形成果(如利润)。故此,做大蛋糕的思维需要长远眼光——善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确有利于投资者,但仅限于长期。对于社会绩效的其他指标也是如此。客户满意度、生态效率和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政策都是公开信息,只是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影响股价。我们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短期利润最大化。在这里,我们还想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短期股价最大化——由于市场效率低下,股价忽略了一些对长期利润和股东价值至关重要的因素。巴菲特说过,“你支付的是价格,你得到的是价值”。这是股东价值不可能“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研究一项决策对股价有怎样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反映它对股东价值有怎样的影响。
市场反应迟钝给企业带来了挫败感。领导者能够在不从股市获得任何直接回报的条件下做大蛋糕。但这种迟钝对聪明的投资者来说颇具吸引力。优秀的企业不见得总是划算的投资。如果一家企业很优秀,而且人人都知道它优秀,投资者得到多少东西,就会花多少钱。光因为“元”(原名为脸书)是社交媒体的领导者而购买它的股票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它的股票很贵。划算的投资指的是,一家企业比其他所有人想到的都更优秀。利益相关者资本就是这种隐秘宝藏的典型例子:它最终会带来利润,但市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些投资者(比如在《商业周刊》上刊文的分析师)沉迷于分蛋糕思维,认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是牺牲股东回报换来的。又或者,他们懂得利益相关者资本的重要性,但认为它难以考量。你兴许知道一家企业有一支敬业的员工队伍,但不知道这些信息会怎样改变你估值电子表里的“利润”栏。
这一结果对社会绩效指标的重要性具有深刻影响。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标准和财务标准是冲突的。为了追求社会目标,如改进职场惯例,股东必须牺牲财务回报。因此,只有兼具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的“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者”才应考虑社会标准。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哪怕是单纯以财务为目标的投资者,也应该这样做——虽然通常会把社会绩效称为“非财务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它往往会变成财务因素。因此,《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将“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与“负责任的投资”进行了比较:后者是利用社会标准来实现纯粹的财务目标。
但我希望更进一步。我们不仅可以去掉形容词“对社会”,还可以去掉形容词“负责任”。考虑社会绩效等财务实质性因素并不是“负责任”投资的专属领域——它就是简单明了的投资。事实上,投资原则——不仅仅是负责任投资——指的是:你只能通过选择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的因素来战胜市场。出于这个原因,社会标准恐怕应该优先于财务标准,因为前者更有可能遭到忽视。
这一观察对投资者教育也有影响。资产管理公司、商学院和专业机构通常专注于教导投资者怎样分析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但它们有责任使这种培训覆盖社会绩效——否则,它们的员工、校友和会员将失去工作。用计算机基于财务绩效选择股票的“智能贝塔”基金近年来规模大幅增长,到2017年12月突破了1万亿美元。如果基金经理和投资分析师希望免遭人工智能取代,就必须培养新的能力,去分析机器无法分析的东西。
为避免混淆,本书仍将使用社会标准进行投资的行为称为“负责任投资”,因为这是标准术语。但我希望,将来再不必这么做——只有当这个概念消失了,我们才能宣称负责任投资已经成为主流。没有“财务投资”这样的术语,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投资决策应该考虑企业的财务绩效。总有一天,企业的社会绩效也将成为理所当然的考量因素。
在实践中,帕纳萨斯奋进基金是负责任投资的一个例子(它的前身为帕纳萨斯职场基金)。它创办于2005年,当时只有一项投资标准——员工满意度。米尔特·莫斯科维茨(Milt Moskowitz)是该公司的顾问之一,也是1984年和1993年最佳企业榜单的共同作者。到2017年,该公司的年回报率为12.2%,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回报率为8.5%。同一年,投资研究提供商晨星发现,在所有投资于大型成长型股票的基金中,帕纳萨斯奋进基金在每一个时间段里(从第1年到第10年)都是绩效最佳的基金。
数字化技术不仅能在建筑施工和建设时发挥作用,也可以贯穿在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中。
人们对负责任投资的普遍担忧是,它可能只在经济上行时才能带来回报;一旦形势艰难,资金吃紧,企业就应专注于短期生存。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危机中,责任也许更有价值,因为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度较低,而通过服务社会建立起了信任的企业可能会获得独特的优势来抵御风暴。
为判断哪种观点正确,我们再次来看看证据。卡尔·林斯(Karl Lins)、亨利·塞尔瓦斯(Henri Servaes)和阿内·塔马约(Ane Tamayo)考察了2007年到2013年间的1673家企业。跟莫扎法·汗及其合著者的实质性研究一样,他们发现,KLD得分高的企业通常并不能跑赢市场。但当他们深入研究金融危机时,发现得分高的企业比得分低的同行绩效要高4%~7%。有趣的是,利益相关者资本的影响,仅为现金持有和杠杆的影响的一半,而现金持有和杠杆可以说是决定一家企业能否度过危机的最重要因素。得分高的企业还有着更高的利润率、销售增长率和人均销售额。在另一个不同的危机时期(安然和世通欺诈丑闻曝光期间),它们的表现同样出色。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疫情暴发后不久,多项研究预示了SRI基金或ESG得分高的企业表现多么出色。这些研究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读者们也欣然接受——但这里确认偏误恐怕发挥了作用。一项研究发现,负责任企业在2020年2月底至3月底期间表现出色,一时间大获称赞。然而,要是研究发现的结果恰好相反,负责任企业的倡导者就会抨击该研究太过短视——一个月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评估业绩。因此,哪怕研究结果对支持者有利,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怀疑态度。另一些分析发现,ESG的强劲表现完全是由于行业效应(ESG投资组合侧重于科技,对能源依赖小),或是未能控制其他变量。
在撰写本书期间,判断负责任企业是否在疫情中表现出色还为时过早。一些学者认为此类企业确实表现出色,但还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此前的经济低迷时期,利益相关者资本获得了回报,跟人们的担忧(也即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只在经济繁荣时期才有意义的奢侈品)并不吻合。但金融危机、安然和世通欺诈丑闻冲击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因此,值得信赖的企业表现优于其他企业是合乎情理的。相比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企业所造成的,故此它不应该使得人们丧失对企业的信任。当然,一些企业的反应是不负责任的,可另一些的反应却是十分英勇。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绩效必定有益于财务绩效,显然还为时过早,但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绩效对财务绩效有害。
将社会绩效与未来的股票回报(而非市场份额、收入或利润)联系起来,让我们更接近因果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虽然我控制了许多其他因素,如行业、规模和近期绩效,但我只能控制可观察到的东西。一些观察不到的东西,比如管理质量,是无法控制的。这里,盈利意外检验能帮上忙。我们有理由假设,分析师在预测盈利时考虑了管理质量——他们一直在跟企业领导者交流,并不断进行评估。既然最佳企业能够战胜这些预测,那么,一定是管理质量之外的东西提高了它们的盈利能力。但这仍然是一个假设,无法直接验证。
了解因果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当企业社会绩效的消息传出时,它的股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消息是企业社会绩效的突然变化,因此不太可能与管理质量、财务绩效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变化相关。事件分析的另一个好处是,这些事件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前一节中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社会绩效的正面指标(如最佳企业榜单),此类指标表明良好的绩效有帮助,但并不能说明糟糕的绩效会造成伤害。
菲利普·克鲁格(Philipp Krüger)研究了1542起负面利益相关者事件,发现这些事件使股价平均下跌了1.31%,即9000万美元。与社区或环境有关的负面事件影响最大,降幅超过3%。战略学教授卡洛琳·弗莱默(Caroline Flammer)关注的是环境事件。正面消息,如某企业推出回收计划,平均能抬高股价0.84%;而负面消息,如排放有害废物,平均将拉低股价0.65%。实际上,有数不清的例子表明,负面利益相关者事件会损害哪怕是全球最顶尖企业看似不可撼动的声誉,反过来也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大众汽车公司在排放测试中作弊、元与剑桥分析公司分享用户数据、富国银行创建虚假银行账户的消息,使得这几家公司的市值分别蒸发了280亿欧元、95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
但事件研究仍然不能完全确定因果关系。即使消息与社会绩效明确相关,它也可能是更普遍的管理能力信号,而市场可能会对此做出反应。如果一家企业排放了有害废物,也许是首席执行官几乎无法控制企业内部情况。所以,弗莱默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并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她研究了投资者提案,即股东要求企业采取特定的行动方案。这种行动有可能事关财务——如支付更多的股息——但弗莱默关注的是与社会绩效有关的提案。2018年,43%的美国股东决议涉及此类问题。所有投资者都要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这种提案并不具备约束力,哪怕提案通过,公司也可以选择对它置之不理,但在通过的提案中,有52%最终得以实施。
这里有两个最近的例子。以下提案是针对汽车座椅和电子系统供应商李尔(Lear)的:
股东们要求公司承诺在其国际供应商和自己的国际生产设施中执行基于上述国际劳工组织人权标准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准则》的行为守则,并承诺采用外部独立监督程序来促进对上述标准的遵守。
另一份提案是针对HCC保险公司的:
股东要求管理层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实施平等就业机会政策,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
提案是企业社会导向的突然变化,不太可能与(比如说)管理质量的突然变化吻合。但仅考虑这一点,并不能解决因果关系的问题。提案有可能来自一家大型投资者的参与——并且正是这一投资者更普遍的参与(并超过了提案的要求)改善了绩效。所以,弗莱默使用了一种叫作断点回归的方法。她比较了以微弱优势通过的提案(得票率略高于50%)和因微弱劣势未获得通过的提案(得票率略低于50%)。李尔公司的提案因49.8%的得票率未获得通过,HCC保险公司的提案以52.2%的得票率通过。一份提案是以微弱优势通过还是因微弱劣势未获得通过,实际上是随机的。这不太可能是由积极参与的投资者造成的,因为这样的投资者会将得票率从49.8%提高到(比如说)70%,而不是52.2%。
弗莱默仔细研究了1997年到2012年间的2729份提案。她发现,较之因微弱劣势未获得通过的提案,以微弱优势通过的提案能让股票回报率提高0.92%。由于通过的提案有52%的概率得以实施,采纳提案能将股东价值平均提高1.77%(0.92%/52%)。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来自做大蛋糕,而非分蛋糕——运营绩效、劳动生产率和销售增长率也在提高,这表明社会导向既能鼓舞员工,也能鼓舞客户。
尽管蛋糕经济学主张对利益相关者的投资最终会让股东受益,但它也强调,进行此类投资需要依据相关原则。以指导领导者了解应该进行哪些投资、拒绝哪些投资。
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原则事关重大呢?莫扎法·汗及其合著者、迈克尔·哈林及其合著者的研究,凸显了实质性原则的重要性。由于外部研究人员很难估计一项投资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故此,考察倍增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十分棘手。然而,我们可以研究一种明显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的常见投资(慈善捐赠)带来的影响。
我们讨论过慈善捐赠会使得领导者选择自己喜欢,而非受投资者、员工或客户青睐的社会事业。事实上,罗恩·马苏里斯(Ron Masulis)和瓦利德·雷扎(Walid Reza)发现,62%的企业向其首席执行官担任受托人、董事或顾问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且,在美国,企业以高管或董事名义进行的捐赠被认为是薪酬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对此信息进行披露。这让马苏里斯和雷扎得以研究这种捐赠的价值影响。如果一家企业首次宣布进行了此种捐赠,并且捐赠对象是与该企业董事有关联的慈善机构,该企业的股价会下跌0.87%。如果套用到104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平均规模上,这就相当于9000万美元。有趣的是,平均捐赠额在100万美元左右。哪怕投资者预料到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捐赠直至首席执行官离任,捐赠额也不可能达到9000万美元。那么,为什么企业价值下跌这么多呢?因为捐赠只是冰山一角。如果首席执行官向跟自己有关联的慈善机构捐赠,他很可能还会在其他诸多不符合原则的方面花钱,从而破坏企业价值。
蔡晔(Ye Cai)、徐瑾(Jin Xu)和杨珺(Jun Yang)单独考察了对与企业独立董事有关联的慈善机构的捐赠。独立董事理应让领导者对绩效负责,但领导者向与他们有关联的慈善机构捐赠,或许会博得他们的好感。蔡晔、徐瑾和杨珺发现,这会让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9.4%。如果慈善机构跟薪酬委员会(董事会决定薪酬的小组)的成员有关联,该增幅会更大;如果慈善机构跟薪酬委员会主席有关联,增幅是最大的。更糟糕的是,如果领导者向与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有关联的慈善机构捐赠,那么,他因绩效不佳而遭解雇的概率会变小。这种自利行为是以牺牲投资者为代价的——股票回报率每年下降2.4%。
这些研究强调了董事会和股东仔细审查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些投资是否符合三大原则。领导者有私人动机进行某些投资,哪怕它们并不满足三大原则,而这么做会使蛋糕变小。
那么,为什么蛋糕经济学并未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采纳呢?因为有必要承认,证据并不全都是对它有利的。
在前面,我提到过帕纳萨斯奋进基金,它是负责任投资成功的一个例子。但这仅仅是一只基金,算不上证据。最具挑战性的不利证据之一是,ESG基金总体上并没有跑赢市场。卢克·雷内布格(Luc Renneboog)、任克·特·霍斯特(Jenke Ter Horst)和章辰迪(Chendi Zhang)发现,在美国和一些欧洲与亚洲国家,ESG基金每年的绩效比市场要差2.2%~6.5%,尽管在控制了风险后,这些差异并不明显。同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独立的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英国和美国,ESG基金的表现与非ESG基金类似,但总体而言在欧洲和亚洲绩效欠佳。从公共投资转向私人投资,“影响力基金”指的是既有社会目标又有财务目标的基金。布拉德·巴伯(Brad Barber)、阿代尔·莫尔斯(Adair Morse)和保田彩子(Ayako Yasuda)研究了过去20年的159只此类基金,发现它们每年的绩效比传统风险投资基金差3.4%。
一些ESG倡导者隐瞒了这些发现。有人在《金融时报》上声称:“ESG策略绩效出众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并不正确,但人们往往由于确认偏误不加批判地接受它。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道德投资行之有效的世界里——我们希望好人赢,我们可以假装不需要处理一切令人尴尬的权衡取舍。《福布斯》上的一篇文章提及一项未发表的元分析,该分析发现ESG策略绩效更佳,并解释说:“通过与对更好的业务、更佳的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感兴趣的人进行多次对话来做出判断,这份新报告的前提是准确的。”但一份报告准确与否,取决于它的科学严谨性,而非那些“对更好的业务感兴趣”(故此也就倾向于更喜欢这样的结果)的人认为它准确。1963年,女歌手曼迪·赖斯戴维斯(Mandy Rice-Davis)曾在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政府名誉扫地的审判中作证,她的证词常被转述为:“他们就会这么说,不是吗?”
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事实:大多数ESG基金表现不佳。但大多数ESG基金或许并不是在实践蛋糕经济学。许多基金利用筛选来评估一家企业是否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如果某只股票不符合某一标准(如董事会多样性不足),或落到了错误的范畴(如属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它就会被筛选出来。事实上,在采用ESG策略投资的30.7万亿美元中,筛选是最受欢迎的方法(占19.8万亿美元)。该方法有三点不足之处,可以解释ESG基金平均绩效为何不佳。
首先,打钩式指标是肤浅的:往好了说,不够完整;往坏了说,易于操纵。说它不完整,举例来说就是,有时人们会用董事会中少数族裔的比例来衡量多样性,但这往往并不能反映董事会思想的多样性或支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文化,更不能反映出这些因素在企业上下是否普遍存在。说它易于操纵,举例来说就是,一家不关心多样性的企业,也可以任命一位属于少数族裔的董事来打钩评判。
其次,按标准打钩筛选是一刀切的方法。它假设更好的社会绩效总是对投资者有利,但这忽视了蛋糕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实质性。莫扎法·汗及其合著者的研究表明,投资于非实质性利益相关者问题并不会提高回报。
打钩筛选法最重要的缺点或许在于它失之零碎,缺乏整体性——如果一家企业不符合一种标准,不管其他方面绩效有多好,其也会遭到自动排除。特别是,大多数标准强调的是“不作恶”(而非“积极行善”),这可能会排除掉整个行业。排除能源股是一种常见的筛选方法,但劳伦·科恩(Lauren Cohen)、乌米特·古伦(Umit Gurun)和阮越国(Quoc Nguyen)发现,较之其他所有领域,能源股产生了更多的和更高质量的“绿色专利”(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能源企业是“棕色”化石燃料资产和“绿色”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的组合,后者的前景有望超过前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即使所在的行业并未被排除在外,“不作恶”的条件也会导致一家创造出了巨大价值的企业遭到筛除。我们讨论过苹果公司怎样提供具备增长和发展机遇的激励性工作环境,但许多社会绩效指标都没有将这一方面反映出来。相反,这些指标往往还聚焦于员工争议。而苹果公司在这方面表现不太好,人们批评它工作时间长、工作文化紧张、向“天才吧”的员工支付最低工资、供应商工厂里的劳工关系恶劣(据说曾逼得一些员工自杀)。诚然,这些争议是负责任投资者应该大力关注的严重问题,但不应该在不考虑积极因素的条件下对其进行评估。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每个方面都完美无缺:同样的企业文化,对一些员工来说是有助于自己扩展能力的激励文化,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高压陷阱。评估员工满意度的复杂性意味着,不能把它简化为打个钩就能搞定的选择题。正确地评估社会绩效,必须亲自下基层——如果你考察的是一家零售连锁企业,你必须去看看它的门店。但一些投资者持有太多股票,没有能力这么做,只能在办公桌上做出这些判断。
衡量一家企业对一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蛋糕分配还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亚马逊是一家做大蛋糕的企业吗?它对客户来说是福音: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成千上万种产品,其在线平台让客户能够比较产品的规格和其他客户的评价。它有助于环保:缩减了开在黄金地段的实体店(而是在土地不太稀缺的地方修建仓库),还允许客户转售二手货(而不再是直接丢弃)。但它对员工的态度就好坏参半了。亚马逊的仓库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伤发生率高,技能培训少。据称,一些工人不敢上厕所,因为距离太远,可能会使他们因怠工而受到处罚,所以他们改用瓶子以备不时之需。与之相对的是,2018年,领英的一项调查显示亚马逊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雇主。亚马逊对环境的整体影响也同样不清楚,因为前述益处必须跟大量使用纸板包装和运输资源这两点相互权衡。
蛋糕经济学包括权衡取舍。做出权衡取舍需要领导者的判断,评估权衡取舍则需要投资者的判断。贴有“社会责任”标签的基金绩效不佳,或许不是因为社会绩效有损财务绩效,而是因为这些基金未能恰当地评估社会绩效。从概念上说,对社会责任投资使用筛选或排除法永远不会带来更好的绩效,因为这只是限制了投资者的可选范围。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投资方法,把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综合起来加以考量。由于综合考量拓宽了投资者用到的信息集合(尤其是将通常遭到市场忽视的信息包含在内),它有可能产生显著的超额绩效。
所以,社会责任投资者的绩效并不能说明社会责任投资的绩效,因为很多投资者可能没有正确地执行。“社会责任投资行之有效”或者“社会责任投资不管用”这类说法没什么意义,因为社会责任投资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东西,一如“食物对你有好处”和“食物对你有害处”这种说法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取决于食物的类型。同样,社会责任投资者的绩效也不能说明社会责任企业的绩效。ESG基金不光评估社会绩效,还会着眼于领导力和战略等传统标准。它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但这些评估可能会出错,一如传统基金经常在这些方面犯错。实际上,传统基金的绩效也逊于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在选股时应该忽视领导力和策略。
另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事实是,“罪恶”行业的绩效优于其他行业。哈里森·洪(Harrison Hong)和马辛·卡珀奇奇(Marcin Kacperczyk)发现,在长达42年的时间里,酒精、烟草和游戏行业的绩效每年都比最密切相关的非“罪恶”行业(汽水、食品、娱乐和餐饮)高出3.2%。但这并不是由于分蛋糕,也即这些“罪恶”行业通过销售让人上瘾的产品从非“罪恶”行业抢走了客户。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应该会赚到更高的利润,而上述研究者并未揭示这一点。相反,他们发现,养老基金和大学等机构投资者会避开“罪恶股”,因为这些机构可能由于社会规范无法持有这些股票。由于只有少数投资者(即那些持有高风险头寸的投资者)可以不受社会规范约束持有“罪恶股”,因此,较高的回报只是对风险的补偿。
最后,即使是支持蛋糕经济学的研究,或许也不能得出普遍性结论。文中提及的所有论文都研究上市公司,因为它们有股票回报——它们减少了人们对反向因果关系的担忧,还可以对风险进行调整。然而,大多数研究还表明,盈利能力有所提高,所以这一结果很可能也适用于私营企业(非上市公司,它们没有股价)。此外,蛋糕经济学的概念性争论并不专门针对上市公司,比如它怎样促成原本有可能遭到否决的长期投资。但私营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联系尚未严格得到证明,希望未来的数据集能够做到这一点。
此外,前述结果或许无法扩展到其他国家。我与卢修斯·李(Lucius Li)和章辰迪一起,把我对美国最值得效力企业的研究扩展到全球范围。全球45个国家都评出过最佳企业榜单。我们找到了另外13个国家,它们都有着足够多在当地设有总部并上市的最佳企业(也即不仅仅是美国企业的子公司),方便对其进行研究。在美国得出的最初结果基本能站住脚——在13个国家中的9个,最佳企业的回报率甚至高于美国最佳企业。
但它们并不总是站得住脚。在法国和德国等劳动力市场监管严格的国家,最佳企业的绩效并不出色。这也有其道理。在这些国家,法律已经保障工人享有体面的福利,如提供解雇保护。如果普通企业已经对员工很好,那么在榜单上最靠前的企业可能会在员工满意度上过度投资。
这一结果很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它强调即使是证据(本书的基石)也有局限性。证据不是证明。证明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当阿基米德证明圆的面积是圆周率π乘以圆半径的平方时,他所证明的不仅适用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圆,也适用于现代希腊的圆乃至全世界的圆。但证据可能只适用于数据被收集的国家或行业,也就是说,能证明美国最佳企业绩效出色的证据,并不意味着它们也能用于证明法国企业绩效也出色。证据还可能存在适用的时间段。未来,股市可能会更快地意识到员工满意度的好处,因此投资者无法在榜单公布后再购买相应企业的股票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其次,研究结果表明,追求社会价值也不应该不受约束。如果投资超过了社会收益大于所支出成本的平衡点,这就是在缩小蛋糕,而不是在做大蛋糕。
这些研究的结论是什么?蛋糕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白日梦。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确实能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长期回报,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做到。所以,尽管企业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但以一种有辨识力的方法来实现也很重要。这种方法的基础是概念和原则,我们将在下文基于证据讨论可行的改革方向,介绍行动计划。
① 许多研究发现,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也可能是反向因果关系——后者导致了前者。研究股价未来的变化,可以削弱反向因果关系,因为财务绩效应该已经包含在当前股价中。
② 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美国最值得效力的100家企业”的股票回报率每年比同行高出2.3%~3.8%(复合回报率为89%~184%)。它们产生的未来利润也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③ 客户满意度、生态效率、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政策,以及在实质性利益相关者议题方面的绩效,也跟卓越的长期股票回报相关。然而,不顾实质性,在所有利益相关者议题方面表现良好,跟卓越的长期股票回报无关。
④ 即便一家企业为利益相关者产生的价值现在就可以衡量,但这一价值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体现在股价上。故此,投资者和社会在评价领导者时须用长远眼光。
⑤ 如果改善社会绩效的股东提案得以通过,股票回报率会提高。对比那些以微弱优势通过和因微弱劣势未获得通过的提案,可以发现一些遭到忽视的变量——这些因素既可推动股东提案,也可拉动社会绩效。
⑥ 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的绩效通常并不优于市场,但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绩效很难衡量,而不是因为它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标准。这凸显了在评估社会绩效时按标准打钩这一方法的危险性。
⑦ 即便社会绩效在一个行业或国家与财务绩效相关,或许也并不适用于其他行业或国家。这也不意味着,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绩效就一定能提高财务绩效。
![]()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蛋糕经济学》一书。)

作者: [英] 亚历克斯·爱德蒙斯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如何实现企业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双赢
原作名: Grow the Pie
译者: 闾佳
出版年: 2022-5
页数: 512
定价: 9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0302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