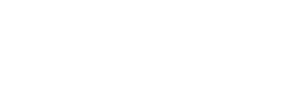幻肢

“观光火车驶过,总会让他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人。
役所真吾边走边垂下义肢,在铁轨上间断地敲击,检查内部的应力。这个活不用动脑子,边敲边算着房贷,去年在郊区看中的一套房子。数字并不复杂,他已经算过很多遍,困难不在这上面。
机修工又算了一遍,意识到铁路AI把他的工资细分到几乎每个动作,因此每敲一下,便向理想迈进了一小步,他挺起胸,然而前面的路也因为精确计算,更显漫长,敲击的节奏乱了。前方观光小火车缓缓驶来,他晃晃脑袋,不去想这事,让到一边,按照公司的规定,微笑欢迎游客。
火车带着风吹过役所的脸,速度不快,他还是本能地眯眼,连同那只义眼,打量车上的游客,在看风景的游客也能看见他。今天是周末,游客很多,几个年轻的妹子穿着短裙,讨论着什么大笑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
年轻真好啊,其实自己也不老的机修工吞咽口水,又想到房贷。这时他忽然觉得看到了什么,车窗的反光晃眼,火车驶走了。他无聊地继续向前走,机械地敲击着。
役所这一天都有点心不在焉,晚上回到在车站附近租的公寓,筋疲力尽倒在沙发上,家政机器人凑过来,帮他把义肢卸下来,换上家庭版。上了一会灵境,打了一局,发挥不好,切换到社区,晃了好一阵,也没妹子搭理他。今天是怎么了,喝瓶酒,昏昏睡去。
难得做个好梦,梦见回到少年时代,和那时的女友约会。她叫什么来着?我一直记得的,役所在睡梦中居然涌起这个念头。他们逛了常去的地方,走过中学门口那座天桥,他伸手在扶梯上敲出一段节奏。走到树底下,岔开手指穿过她的长发,有一根细小的叶梗粘在上面。
然后他们去了公园的小树林,那里已经有好几对,大家默契地互不打扰。他们找了一个幽静的角落,把女孩挤到墙边,自己的手岔在她头顶,手背的刺青很显眼,嗯,这叫壁咚,睡梦中的分身又嘀咕道。 女孩的脸很红,自己心跳得厉害,手不听使唤地伸到女孩衣服里,抓住柔软的胸,感觉真好……忽然感觉有些奇怪,把手缩回来,翻过面看……
役所猛地惊醒,大口喘气,早上在火车上看见的,他还不确定是什么,白天一天的状态很怪,多半和这事有关。他爬起来,抓起酒,还有半罐,又放下,找了水喝,调出义眼的工作纪录,投在半空中。他拖动进度条,到大致的时间,早上的第一班列车。
机修工找到有印象的短裙妹子,定格,一个一个游客地找。最后停留在一个老头身上。看着像成功人士,穿着夏威夷风的花衬衫,半截袖露出整个小臂,手背上有个刺青,老虎嗅蔷薇,他那时很中二,念过一阵诗,就纹了这个刺青。这是他的手。
役所抓起酒慢慢啜,不应该,按照换肢管理条例,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而是在大洋彼岸的什么地方。不过这里是热门的旅游线路,也不奇怪。机修工圈定人像开始检索。
工作纪录保存六周。四周以前的周末,义眼第一次捕捉到老头,以后基本每个周末形成惯例,都是早上第一班,显然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役所努力回忆,五周前的那个周末,他正好倒休,中间还有一个周末,不在状态,没有对列车行注目礼,被扣了钱。机修工熟悉线路,老头应该是去山上泡温泉。他确认这个事实,把剩下的酒灌下去。
一周以后,役所目送火车过去,一直盯着老头,老头茫然地看着远处,没有注意他。老头从来没有同伴,看起来一个人生活。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老头,都忘了心仪的房子。
得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算什么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下一个周末很快到来,机修工请假,订了车票和温泉酒店。在这条线路上工作这么久,还没有去过终点,第一次作为游客体验自己的服务。他也很久没出过远门,或者出席正式场合。
役所梳洗干净,刮了胡子,卸下家庭版义肢,换了一副去夜店的,透明外壳,里面镶嵌闪光的器件。取出唯一的一套正装,在衣柜里搁了很久,比了比,太正式,又放了回去。虽然他还没想好干什么,但是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最后还是穿了一套和大家差不多的休闲装。
机修工搭机务段的车到前一站上车,坐了会,起来穿过车厢,假装不在意地寻找。走过两节,坐在老头对面的妹子注意到役所,他也瞟了她一眼,有点心动,女孩很可爱,是他喜欢的款,老头背对着他,还在看窗外。
役所忽然灵机一动,凑上去:我能坐这么?我那节车厢有个人抽烟,不听劝阻。老头抬起头,看看机修工,又看了一眼女孩,女孩把她放在小桌上的手包收回去一点,老头发话,年轻人坐吧。段注意到女孩没有换义肢,不知是做什么的,或者还没成年?
机修工成功实现搭讪的第一步,但是他不善交际,不知接下来如何推进,想问老头的目的地是哪里,刚说出一个字,女孩抢先问,这种人最讨厌了,你怎么不叫列车工作人员?
役所有点紧张,不知她是真心问,还是试探自己,我就在铁路工作,同事们很辛苦,就不打扰他们了。说完就后悔,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赶紧补一句:不过我不在这个车段,是来温泉旅游的。女孩看看他的义肢,我还以为你是搞艺术的。她职业地介绍,我就在温泉酒店工作。怪不得。
一会我还要收拾一下,不能亲自接待您,很遗憾,不过可以给同事打招呼,给你折扣。等你再出来,我应该就到岗了,还可以给您别的优惠。不愧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敏锐地把握到机修工的疑问,平时周末我们得在酒店值班,昨天我回大都会办点事。
你具体做什么?这么结实,是火车司机吧?这话其实隐含冒犯,但机修工不以为意,笑起来,不是司机,他指向窗外掠过的一个界桩,我是机修工。女孩这么坦诚,他也顾不上要对老头掩饰。不料也提起老头的兴趣,转过头来,你这个工作很辛苦吧。
老头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机修工的闪光义肢,役所看看女孩,解释,这是出来玩。他打开义肢的投影端口,给他们看自己的工作义肢。说到工作,一点也不怯场,讲了很多。一老一小看起来听得津津有味。
役所适时地打住,终于轮到他问了。您是做什么的?一看就是成功人士。老头摇摇头,脸上却不无得意,我退休前是会计师。机修工和前台同时露出艳羡的表情,心想一定挣得很多。我在海外做了好多年,最近刚回来。
役所追问道,脑力工作者要装义脑吧,本来就聪明,装上更聪明了,心里想的是,一定很贵。女孩也露出好奇。老头犀利的眼神收回记忆,是啊,做我们这行尤其需要,我一开始装的老版本,和人脑的适配度不够,用一会儿就头晕,得停下来歇歇。过几年换了新版本。不过现在退休,还是摘除了。那玩意只能工作,不能帮助人体验人生。
役所心中狂跳,终于进入正题。你们脑力工作者不用换义肢,真幸福。我那双铁手光重量就吃不消,还要做各种操作。确实他的义肢在技术工种中也算复杂的。
老头苦笑,我们也要换义肢的,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会计师每天处理大量信息,光靠义眼输入是不够的,特别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要负责原始数据。我们的义肢和你们的专业化方向不一样,有高速扫描端口,还有计算模块,辅助义脑……就像恐龙,你们以前学过吧,体型过于庞大,在身体的不同部落分布着副脑。
役所已经忘了中学博物课的内容,女孩也差不多,那恐龙的副脑要是和主脑意见不一样,一个想去这边,一个偏要去那边,恐龙就一个身体,该听谁的?三个人想象恐龙身体纠结的样子,不禁都笑了。
役所把话题拉回来,所以恐龙被哺乳动物淘汰了嘛,老虎嗅到蔷薇,就直接走过去。老头摊开手背,我退休换装时,社保署的网站显示,这个原肢有刺青,可以打点折。机修工心中一震,给他换义肢的医生正是这么说的。
他强作淡定,看看老头,没什么异样,接着说,我倒不是图便宜,虽然这个年轻人有点中二,我也年轻过,回到那时应该也喜欢这个寓意。年轻人纹这个是酷,老人家纹这个,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也适合退休的状态。女孩称赞老头一点也不老。
刚换上的时候,感觉有点怪,义肢我也戴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没有的话,和义肢差不多,但是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刺青,总是提醒我,这是别人的手,这个社会是这样运行的。我已经退休六年,看久了就习惯了,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仿佛就是我从小长的手,青春期叛逆的举动。
役所心情复杂,面无表情,女孩陷入沉思。三人陷入一阵沉默,然而并不尴尬,女孩先打破,工作都不容易。你们可能看我没有改装过,游客们需要一种田园,回到故乡的感觉,工作人员就像赛博朋克时代之前的人一样纯朴,可是他们还同时要求这个时代的服务标准,不考虑这两者其实是矛盾的。
我身上的改装都是隐蔽的。她指向自己的脸,这个像美瞳的,就是义眼,可以扫描游客面部,识别身份,让我能马上叫出他们的名字,特别的习惯,曾经一起出行的亲友,等等。游客觉得自己受到重视,心情就会好,就有更大的机率重新入住。
女孩又张开纤细的双手,手总是会出汗,分泌油脂,还会沾染细菌。工业时代的酒店业,都是戴白手套,但是手套还是有卫生的问题,也显得陌生,不符合现在的服务理念。我的手做过手术,在皮下植入纳米机器人集群,可以在工作时间封闭皮肤,清理表面的微生物。
老头感慨技术进步,他从没听说过。役所幻想握着这双手,被它抚摸,忽然从手上传来异样的骚动,像很多蚂蚁爬过,不禁生出寒意,对她的欲念去了很多。
三人渐渐熟络,一起下火车,搭摆渡车去酒店,在大堂分开,互相加了社交账号和名片。老头名叫管谷庄太,女孩名叫安室奈由里。
办理了入住,役所没有去找由里,躲到角落一个小池子,沉进热水,只露出脑袋,胡思乱想。我来这里做什么,居然和老头加了好友,还勾搭一个妹子。机修工放松全身,在水里浮起来,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脑海里涌现,我想拿回我的手。
又出现两个声音,围绕这个命题展开辩论。这本来就是我的手,是的,是我签字把它换掉了,并且拿了补偿的费用。人人都这样做,我也是迫于社会压力。如果他一直呆在海外就好了,看不见我的手也不会想。问题就是现在看见了,我不能当作没看见……
役所忽然想到,很多年以后,自己也会退休,他以前没考虑过这么远的事情,他还年轻,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他想象不出自己到那时会是什么样子。也会有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进入职业轨道,安装专业化的义体,把原肢换给他。为了避免被人找到,他一定不能要带任何特征的。
但是新闻报道人口在持续减少,也许到时没有足够的原肢供应,他得带着义肢度过余生,带进坟墓里。这个老头已经享受过人生,挣很多钱,受人尊敬,有丰厚的退休金。役所忽然生出仇富的心理, 又觉得这样不对。
役所又想起小时候,他和别的小孩一样,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当科学家,医生,警察,自己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学业也是中等,中学毕业只考上技术学校,就决定了之后的路。毕业之后也不一定要做机械相关的工作,但是都要专业化。如果当时选了别的工作,别的公司,就不会遇到这个老头。
役所家只是普通的企业职员,正好那年铁路公司招人,他试试,居然被录取了。拿到通知书,他就预约了换装义肢。毕业季手术排地很满,几乎都是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很紧张,还有男生哭。役所自认是感情比较迟钝的人,抱着赶紧完成任务的心态,躺上了手术台。记得有个圆脸的女护士安慰他。
做完手术,恢复一个月。他很快熟悉了义肢,接受铁路公司的培训。专业化加强与业务相关的功能,他能感受到义肢的强大力量,但是牺牲了原生身体相对平均的全能,无法形容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他做过好几次梦,梦见原肢,医生说这是正常情况。
有少数派拒绝专业化,机修工身边不认识这样的人,只看过新闻报道,或者是权贵,或者只能做一些特殊,或者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当然薪水也低。他回想在大都会街头看见的流浪者,好像确实没有装义肢。几年前警方还破获过地下反抗组织,恐吓人力资源专家,爆破义体生产线。之后再没人追随他们,很快被公众遗忘,人们要讨生活,他们只会破坏,提不出替代的方案。
役所内心斗争了很久,也没有结论,但还是强烈地想要自己的手。那么先不考虑正义的问题,我能怎么拿回它呢?机修工打开义肢的计算端口,搜索“抢劫义体”,跳出一大堆新闻。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存在一个赛博器材的黑市,专门负责抢劫的团伙,被称为“义体猎人”,他们主要对昂贵的高性能模块下手,又派生出将模块外观修饰成经济型的市场机会,当然骗不过这行的老鸟。
人类一直有审美自身的需求,义体问世以后,扩展了打扮的空间,有土豪用贵金属和钻石装饰义体,成为不法之徒的目标。还有无意中纪录了隐私和犯罪证据,被人销毁,甚至灭口的,纯粹恶作剧,等等。这个时代义体是如此普及,就关系到人类方方面面的欲望和冲突。
役所开动脑洞,伪装成抢劫团伙?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武力,虽然对手只是个老头。万一下手太重致死,谋杀是机修工绝对不敢想的。
一个思路冒出来,虽然义体一般设计成防水,泡温泉的时候,很多人会卸下来,存在更衣室。既然已经认识,能够接近目标,可以用药物令其长时间昏睡,把原肢换一套义肢,别人不会注意,等老头醒来发觉,别人会以为他老糊涂,和别人拿错了。那个粗心的客人也不会出现。
机修工为罪恶的念头激动,反复想了又想,等天色渐晚,别的游客都去吃饭了,才走出浴池。下面就是执行了。
役所从网络图书馆下载了人体工程学资料,医学和机械的跨界学科。和铁路电气设备也有相通之处,恶补了几天,换装原肢当然不可能完全复原,还是以义肢的方式处理生物活体,可以方便地拆装。规划地好,可以一击得手。
役所在暗网上订了迷药,又找到赛博黑市在大都会的一家门店,经过一番试探,用假账号付了订金,订做一对仿生义肢。机修工乔装打扮,赶到市里,半夜小心摸到接头地点。居然是一家成人用品店,门口闪着艳俗的广告,他在门口转了两圈,快步推门而入。
长廊尽头一个猥琐的家伙正在调试赛博娃娃,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看手上的活挺熟练。役所对上暗号,那人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后面取出一个包裹。店里的灯光不对,役所打开义肢的射灯,店员赞道,挺专业。役所把两只手仔细看了一遍,你也挺专业。
店员看他这么细,补充道,指纹是个死了的男人的,查不出问题,带着一种看穿的神情,役所猜店家认为他要换上这双手,去干什么犯罪勾当,不动声色,交了尾款,带着货赶紧溜走了。
下一个周末,役所带着鲜花,出现在温泉酒店,对由里展开攻势,这样他就有正当的理由创造与管谷的偶遇。他没有刻意表现,让老头自己猜出来。再下下个周末,役所的追求就遭遇“挫败”,顺水推舟地去找过来人开解。
管谷慷慨地请他吃了法式大餐,订了一个温泉包间,又叫了清酒和海鲜。役所心中狂喜,机会这就来了。两人围在池边,边吃边聊。你的眼光不错,那是个好女孩,能娶回家当老婆。不要像我这样,年轻时光顾着忙事业,说是事业,也是帮别人数钱,不是理想的工作,倒是挣了些钱,然而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一直在国外,难得碰到本国人,其实中间也遇到过几个,回国相过亲,还交往过一个洋纽,但是工作忙,主要还是我心态不对,总觉得还有机会,一来二去都没下文。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自己已经老啦!就算按行业的平均年龄结婚,儿子也该有你这么大了。
管谷畅开心扉,讲了很多。役所听地出神,把藏在义肢缝隙里的迷药给忘了。
又一个周末,役所工作了一天,由里让他下班后去酒店找她。他们已经初步确定关系。机修工想,是该像管谷先生教导的,考虑终身大事了。对于管谷,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想再见他,听他讲人生,又想到他曾经打算对管谷干的事,感到很羞愧。他来不及换装,提着工具箱去了酒店。
酒店前面的广场上开始周末例行的表演,演员跳着动感的舞蹈,吸引了大部分游客。役所拥着由里,在酒店的侧面露台上看,这里视野很好。他转头看见管谷进了配楼的酒吧,背影颇显落寞,不由地抱紧由里,由里幸福地靠在他怀里。
突然周遭的世界一阵剧烈抖动,两人几乎摔倒,有人喊,地震了!主楼晃了晃,落下些杂物,轰的一声,配楼坍塌了,它顺着地势建在一个坡上。役所伸头看了一眼,放开由里,向楼下狂奔。身后传来由里的呼叫,真吾……役所先生!役所脚下缓了一缓,马上又加速,一眨眼跑得没影了。他知道,这段关系完蛋了。
役所跑到废墟前,配楼完全解体了。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大声呼救,他找到位置,伸出义肢,抓住一块墙体,义肢的引擎发出呼啸声,抬起抛出。他又移开一块,女人完全露出来,穿着制服,是酒保。他把她抱出来,酒吧看起来还行。她指着废墟,里边还有个老人!机修工把她放到安全的地方,又跑向废墟。
管谷被压在废墟最厚的地方,二楼屋顶保持很大一块结构,超载的红灯亮起,还是无法移动。役所转了一圈,找到个空隙钻了进去。破开几处障碍,到了管谷身边。他状态很不好,全身多处被砸伤,微微睁开眼,真吾你来啦,昏了过去。
役所抓起一只手,呆了呆,骂了声混蛋,撕开一块桌布,把管谷和自己的上身绑在一起,慢慢爬了出来。人们鼓起掌来,酒店的医生提着急救箱跑过来处理。又过了一小时,山下的救援到了,用直升机把管谷送去大都会中心医院。
役所受了点皮外伤,在郊区医院留观一晚,第二天起来,正想了解管谷的伤势,中心医院打来电话,很遗憾地通知您,管谷先生因为伤势过重,于今天早上8点21分去世了。役所颓然坐倒,用尽力气说,如果在本地举办葬礼,请通知我。
役所情绪回复过来,意识到有机会去太平间偷原肢,但是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麻烦不说,他决定救管谷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管谷先生孤独终老,就让自己的手送他一程吧,役所喃喃道,就请把我当作您临时的儿子吧。
一周后,在郊区公墓与管谷先生告别。管谷只有一个海外留学的侄女,赶不回来,委托区公所代办葬礼。礼毕,区公所的法务官拦住役所,管谷先生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他在海外的不动产和基金留给他的侄女,他在国内的现金及其它权益留给您,感谢您救了他的性命。
役所恍惚道,我没能救回来。法务官说,据护士转述,管谷先生的意思是,您冒着危险救他,让他在人生最后的时间不孤单。法务官递过来终端,是整理的财产明细。役所看了看,现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顶他两年薪水,还有一些衣服,家具,房屋和汽车未到期的租约什么的。
还有一页,役所翻过,不禁瞪大了眼睛。这是怎么回事?法务官解释,对于换装原肢的性质,法学界存在争议,一派认为属于人身权,是遗体的一部分,另一派认为等同于义肢,是财产。我的老师是财产派……既然管谷先生明确说国内的全部权益,理当也由您继承。
得到这笔不菲的遗产,温泉酒店和铁路公司又给他发了奖金,役所付了首付,开始还贷的漫漫征程。但是工作的时候,他不会想这件事。观光火车驶过,总会让他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