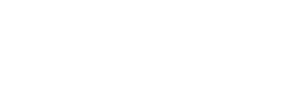惊奇与忧惧: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催眠术

【作者简介】张邦彦,毕业于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为台大医院住院医师,现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心理科学史、医疗史、东亚近现代史、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等。
1905年的某一段时间,上海《申报》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同样一则广告——长命洋行的疗病神带。一名留着络腮胡、身穿西装的外国人用双手捧着一条电带,电带放出无数电气,射向打着赤膊、留着长辫的中国男子。再仔细一看,男子的腰上也缠着这么一条电带,电带上有电钩交通电流,电镖控制开关,电线则连接到铜箍,铜箍贴着命门、丹田、肾部,让电流直达脑筋、下通涌泉、旁及奇经八脉五脏六腑。广告图像周围环绕文字,开头写着:“本行所售之电气药带乃著名西医麦克劳根所创制。”电带号称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从身体羸瘦、小便赤涩、月经不调,到伤寒、肺结核、瘫痪。
之所以在本章的开头提起这一则广告,我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多了解一项过去的新商品,而是希望借此挖掘某种较深层的意义关连,以呈现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的其中一面。中国的现代性,如李欧梵所言,涉及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让“今”与“古”成为对立的价值,并且将“当下”视为与过去断裂、连接辉煌未来的转折时刻。晚清民初的数十年间,是现代性意识萌发的关键年代,新事物接二连三地到来,人们的经验之流暴露于不断的惊奇之中。而这些新事物并非单独地被接受;相反地,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整体的转变下,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把握个别事物之间的关连。电带这项医疗商品,就跟本书要探讨的催眠术一样,是在一种新的身体论述浮现的前提下,才在中国社会里获得广泛的接纳。这种新的身体论述,我称之为“电磁化的身体观”,它形塑大众的现代性经验,并使催眠术获得新的认识可能。
当我们细看电带广告的内容,会发现里头主张:世界中的物质无不带有自然电气,而人体的精神气血亦有赖电气维持,透过电带由外而内补充、调节人体电气,即能够增进健康,缓解病痛。再考究长命洋行的产品来源,可知它来自19世纪末美国芝加哥Dr. M. L. Mclaughlin公司出品的Dr. Mclaughlin‘s Electric Belt。这类电气医疗产品风行美国并畅销中国,是一个时代集体心态的缩影,无论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爱迪生电力网络,或者20世纪中国的口岸城市、殖民地台湾,人们不断目睹电气化带来现代生活的改变。[一个例子是台湾画家陈澄波(1895—1947)的作品,在多幅画作中电线杆都是重要的构图元素,引导观画者的视线。而在画家潘思同(1903—1980)的重要画作《上海南京路》里,电线也主导了画面的分割。]一名研究者曾经用“电气神学”(electric theology)来形容当时人们对电力的崇拜,仿佛在它所及之处赋予一切事物生命与力量。李欧梵在他知名的《上海摩登》里也提到,上海的摩登作家们“沉醉于都市的声光化电,以至于无法做出任何超然的反思”。声光的新形式感官体验来自电气的发明,电磁相生,“电磁化”可说定义了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面向。
我们在此看见事物之间的关连:电力设施作为外部技术系统,提供人们视觉、听觉的新刺激,而身体对电流、磁力流的体验则成为内部的对应。疗病电带以有形的方式创造电流交通的身体感,而催眠术则带来无形的内在电磁体验,许多人形容感应到能量在躯干四肢流动,甚至设想脑筋能够放射电磁波动。就此而论,现代性不只由物质的现代化所促动,也牵涉人们的身体意识及身体想象上的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身体观绝非一朝一夕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递、接触和抗拒后,才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产生广泛影响。电磁化身体观最早在18世纪的西欧萌芽,1773年,维也纳医师梅斯梅尔宣称在治疗个案奥斯特林小姐身上发现了先前人们不曾察觉的物质——动物磁力。这位催眠术的先驱指出,宇宙间布满流体,且“天体、地球和有生机的身体间存在交互影响”,疾病产生于磁力流的不均匀分布及阻滞。他的磁性催眠学说吸引无数追随者,并扩散到西欧各地。19世纪30年代,磁性催眠术从欧洲传入美国,昆比继承这项磁化治疗,许多昆比治愈的病患描述催眠过程像是“抱着一颗电池站在绝缘凳上”。 1851年时,美国催眠师多兹甚至出版一本名为《电气心理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lectrical Psychology)的著作,以正负电性来解释疾病的原理。这套疾病的电磁解释,影响了后来疗病电带的发明。
不过,电磁化身体观却没有紧接着在中国出现,而是要等到19世纪末。这段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差,不是来自知识或技术在传递上的延迟,而是过去天朝的优越心态,使得新的身体观缺乏适合的出现条件。事实上,中国人在梅斯梅尔发展出这套治疗的10年内就对此有所听闻。1783年8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致信给巴黎的耶稣会长官贝尔坦神父(Abbé Bertin),表示在中国发现了一种跟梅斯梅尔的磁性催眠术非常相似的学说——中国功夫(Kongfou chinois)。“倘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尧舜、黄帝、神农乃至伏羲的时代,有一种差不多类似于梅斯梅尔的磁性催眠术的治病方法,那么无疑至今仍有一些还流传着。”他还指出,梅斯梅尔的理论中的磁性双极即是太极系统里阴阳的特殊、附属形式,而气的不平衡则造成疾病。钱德明的观点除了来自自身观察,也很可能来自他跟中国人沟通的经验。而19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出版的《外派传教士教化书信选集》更印证了这点,一名传教士写道:
他们〔中国人〕总是希望说服我们,所有对社会有用的科学与艺术都是在欧洲人动念之前的几世纪创造于中国。一个很简单的证明就是:磁性催眠术的发现应归功于他们。这门技艺被他们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而即使到今天,那些道士仍显示他们比我们的梅斯梅尔及其他法国磁性催眠专家更加优越,不管在理论或在实作上。
由此可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人对催眠术并非全然陌生,而是不具有跟西方人相同的心灵去赏识其中蕴含的电磁学说,也因此不认为催眠术有任何特殊之处。在他们的观念里,身体本应经验到的是气的失调——匮乏或过剩——而不是电磁力的灌注,如同莱顿瓶(Leyden jar)、伏打电池或电磁铁的运作;博大精深的气与阴阳,即可以涵纳、解释传教士口中催眠术的一切。这样的差异不令人意外,前现代或现代早期的东方人与西方人拥有不同的身体语言、感知,乃至身体存有论,已是许多人所认知到的事实。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方科技展现了它的物质优势,西方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的挑战也逐渐让人无法忽视。这不只是知识、概念上的冲击,也同时是具体经验的转化;一种由“气”到“电气”“电磁波动”的现代身体意识于焉出现。直到此刻,催眠术才有机会在中国获得现代的、与功夫分离的意义,跻身新事物之列。
而催眠术之现代意义的浮现,也必须归功于“nerve”概念的转变。[1]虽然早在明初以来的医学文献中就已经有此解剖学上的描述,例如《回回药方》便已出现“筋头是脑”的说法。但nerve一直被形容为“气”的运行路径。[2]即使在19世纪50年代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编写的《全体新论》里,nerve都还是与“气”脱离不了关系,被译为“脑气筋”。直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电生理学的引入,nerve才逐渐连接上“电”的法则,例如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在《格物探源》里写道:“电学之出也如此其艰,功用如此其巨,究不知此事早具于吾人之身,自有生民以来,无一人之体非此电气之流动者。电报之铜线,在人即为脑气筋。”以及被麦仲华收入《皇朝经世文新编》的一篇文章亦记载:“请言脑气筋为电学之理,其质非筋、非肉、非脃骨,而如管而柔、如丝而白,外为胞膜,内为精髓,分布于五官四体,无时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觉,一司运动,咸通于脑,故名曰脑气筋。”透过将nerve比拟为电线,神经电学提供人们一套新的语汇、新的语言再现方式,也创造新的认知及感觉模式。
谭嗣同(1865—1898)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仁学》里,我们能清楚看到电磁化身体观对他产生的影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诚如不少学者指出,《仁学》混杂了西方科学语汇与儒、释、道、墨等各家之说,“电”“以太”已非原始西方科学的概念,必须放在“仁”“心力”等观念下予以解读。虽然电磁化论述的影响力在《仁学》中被凸显了出来,但传统思想中“气”的成分仍未消失。一方面,他吸收了神经电学的知识,将有形的脑与无形的电相类比,并视电气为宇宙万物的媒介。他写道:“电不止寄于虚空,盖无物不弥纶贯彻;脑其一端,电之有形质者也。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如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另一方面,谭嗣同也用“电象”来形容自己的静坐体验:“信乎脑即电也。吾初意以为无法之动,继乃知不然。当其万念澄澈,静伏而不可见;偶萌一念,电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动不止。”
在当时,谭嗣同绝不是拥有这类经验的少数人,但他的文化涵养让他有能力将各种外来的影响纳入一套思想架构之中;相较之下,许多中下阶层的庶民也受到类似的电磁化身体观的影响,但他们不是透过有系统地阅读西学书籍,并形诸思想表达,而是透过散落在生活中各种片断的活动,来接收或展现他们对新观念、新事物的态度。比起专注于思想性的讨论,本章更关心后者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意涵:催眠术和电带、电报、电气设施等新科学、新技术,在日常层次上广泛地组织了市井百姓的现代性经验。
近十余年来,近代史学界已有丰富的著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描绘大众所置身的现代场景,以及政治、知识与生活的相互渗透。本章延续这样的学术旨趣,选择从大众科学的观点切入,呈现华人社会里的催眠术活动与现代性经验交织的情况。在一个热烈欢迎科学的时代,催眠术显示了它的争议本质,鲜明地反映出人们正负两极的观点与情感。以下的内容,我首先希望厘清:在电磁化身体观兴起的背景下,催眠术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究竟透过哪些管道、基于哪些理由,在华人社会(至少在大城市)里获得如此广泛的回响?其次,我则要回答:为何催眠术仍未获得完全正面的评价,反而令许多人感到忧虑和畏惧,甚至引起政府的压制?

催眠术能够在华人社会中广泛传播,必须归功于三个主要管道:新式出版物、展演、讲习会。其中,清末大量出现的报刊无疑是将催眠术再现为新兴科学,并传播到民间的最基础媒介。
自1895年开始的往后20年,是张灏所谓中国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在这段期间,随着士绅阶层的政治改革、现代印刷技术与出版事业扩张,新式报刊杂志大量出现。尤其在戊戌变法后,白话报刊和商业报刊的数量快速增长,五四白话文运动则掀起另一波出版高峰。[3]在甲午战争之前,报刊以外文报、文言报为主,白话报刊仅只《民报》一家;维新时期则陆续出现至少五种;到了革命前后,白话报刊成长到近两百种。另外,根据一份时人的统计,到了1917年,林林总总的中文报刊多达两千种发行,其中四百种的影响力超出地方层次。这些新式报刊扮演启蒙“下层社会”的重要功能,尤其白话报刊的简易文字,让粗通阅读的劳动阶层也能掌握新知与时事。这些媒介对知识传播的影响力不容低估,根据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统计,清末具基本识字能力的大众,男性即有30%至45%,女性则为2%至10%。[4]即便仍有许多不识字的妇女或工人,他们也习惯于在家庭或工厂中听人读报。[5]除了白话报刊之外,画报的出版更提供思想传达更直观且生动的途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为: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综观这段时期,通俗文本对现代政治观念与科学知识的普及起了关键作用,催眠术蕴含的猎奇特质则成为这些媒介的热爱题材。
最先有办法透过报刊接触西方催眠术的当属在华传教士、官员与商人,英文报刊对催眠术的着墨大约比中文报刊早了10年。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英人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就开始出现催眠术相关题材,介绍法国医师沙可对催眠术的最新发现。报纸描述沙可利用磁铁接近两名背对背的患者,使她们进入磁力睡眠,并成功让其中一人的症状转移到另一人身上。[6]同一时期,香港的《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也报道法国医师吕伊斯(Jules Bernard Luys)向医学会成员报告受催眠者对各种物质的反应。在一群科学家的见证下,吕伊斯将装有番木鳖碱(strychnine)的试管交给隔壁房间的催眠受试者,受试者对内容物一无所知,但接获指示将试管置于左侧颈背。不一会儿,受试者的左颈肌肉开始收缩,接着抽搐,并呈现身体僵硬。当内容物换成大麻树脂(hashish),另一名受试者则又产生截然不同的表现。[7]20世纪初期,这些英文报纸也率先介绍不少有趣案例。一篇报道提到一名工人的右膝被半吨重巨石滚落擦伤,尽管伤口轻微,他却再也无法移动右脚。此事上了法院,医学鉴定报告表示工人的症状出于震惊后的自我想象,法庭于是指派二名医师对工人施行催眠治疗。另一篇《士蔑西报》(The Hongkong Telegraph)的消息则是宣告催眠术取代传统手术麻醉,一名英国中年妇女在催眠状态中顺利完成腿部截肢。
中文报刊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刚开始报道催眠术时,也几乎都取材自外国的消息。这个现象显示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本土仍鲜少有催眠术活动可供报道,大众对催眠术的热情一开始是靠国外趣闻才被撩拨起来的。另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报纸报道的内容并不涉及施展催眠术的“人”,而是借“机器”来完成催眠,这与身体观的电磁化转变高度呼应。1898年在《知新报》上的报道即为一例,这份维新派报纸将催眠术放在“格致”的栏目中,与植物学、化工学等文章并列。报道介绍了几种解决失眠问题的催眠机器,其中一种是由美国穵森敦的哈闷特医师所研发,透过施用电气于枕头和铺盖进行催眠;另一种机器是安装二面镜子的箱子,借由镜面回转,让光线闪射在受术者的眼上,使眼睛渐疲而达到入眠效果;第三种机器则呈柱状,置于受术者脑后缩减动脉血流,以达成倦怠欲眠的目的。不过更多时候,刊物则是报道催眠术的神奇效果,像是介绍莫斯科医士巴哥吾利用催眠术疗治酒癖,效果更胜其他疗法;或是介绍日本教育界将催眠术施于儿童身上,发现学习识字的成效更胜以往。有些报道更强调催眠术的多重好处,包含劝捐、禁赌、弭盗、饬吏、兴学等妙用。
鼓吹催眠术功效一段时间后,报刊的编辑们又再发掘一类更猎奇的新题材——动物催眠。催眠术不只能够由人类施展到其他物种,有些动物甚至也会使用催眠术。这类主题同样与“激动”“频率”等神经电学的观念脱离不了关系。《东方杂志》曾经刊出《动物与催眠术》《蛇与催眠》等论说文章,指出催眠术可以施于鸡、昆虫、蜘蛛、老鼠、牛、马等动物,当这些动物因神经受到过度刺激与压迫,便会全身硬直、静止不动。而蛇类则经常被形容为具有迷眩的天赋,它们借由头部与身体固定频率的摇摆、旋动,搭配睒睒目光和斑斓鳞片,激动猎物的神经系统,继而产生催眠效果。这方面的题材不断引发读者的兴趣,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诸如《科学画报》《知识画报》《新中华》《天津商报每日画刊》《东方画刊》等报刊,都仍不时可见它们以图画呈现外国研究者对猩猩、猴子进行的催眠术实验。[8]
上述这些报刊的属性大多以传达时事、普及科学知识为目标,讲究可读性、娱乐性的同时,尚不至于过度夸大。但有些刊物倒赋予了这个题材更丰沛的渲染力,来回于虚实真假之间。像是《家庭良友》这本妇女杂志便曾经刊登“一篇真实的童话”,叙述俄国的动物心理学家杜洛夫利用催眠术训练动物,并为这群动物打造社会主义农场,教导每种动物不同的技术,包括伐木、起重、播种、烹饪。在杜洛夫教授临终之际,他训练的60只老鼠甚至鱼贯而出向他行告别式。
而除了纪实与论理的报刊新闻、虚实难辨的杂志故事,还有另一种文类——新小说——是不能忽略的。晚清兴起的科幻文学适足以证明催眠术所具备的科技吸引力。东海觉我(徐念慈的笔名,1875—1908)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与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并列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作,而前者即是一部结合身心分离、动物磁力、脑电等相关元素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全文一万三千余字,出版于1905年。故事的主人翁法螺先生自承因终日苦思学术的难题而不得其解,在“脑筋紊乱”的状态下不由自主地登上高山之巅,霎时间感受到“诸星球所出之各吸引力”,身体中的各种原质随之分合,在一阵昏迷后产生灵魂与躯壳的分离。法螺先生的灵魂从此展开畅游世界各洲及宇宙星球的浩瀚旅程,他一面思忖如何利用灵魂的能力挽救羸弱的中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 [9]
从小说情节一开始对星体与身体间吸引力的描绘,我们不难发现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理论的身影。而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催眠术又再度登场。法螺先生的身心重新合一,坠落于海,幸运搭上一艘战舰回到中国,见到“上海有开一催眠术讲习会,来学者云集其中,最元妙不可测者,为动物磁气学,又触余之好奇心,拟于此中开一特别之门径。”受到催眠术启发的法螺先生于是兴起念头,想要利用大脑自然的感应能力发展“脑电”,取代人为的电信、德律风和无线电,并吸引全世界的人前来学习。无奈的是,他的脑电实业计划最终受到电信、交通公司与失业劳工激烈的攻讦,只好不得已搁置,潜回乡里暂避风头。
从外文报刊、中文报刊、画报到科幻新小说,这些新式传播媒介在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十余年间,以不同面貌将催眠术带进中国,呈现给不同的阅读群体。催眠术在民间的普及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媒介的兴起;而反过来说,催眠术之所以获得这些新式媒介的关注,亦在于其本身具有足够的话题性。从内容观之,催眠术成功结合了电气、磁力、脑神经等当时最新颖的科学词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正经八百的科学文章通常无法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但催眠术的特性却能让论说性的文章添上一层神奇的色调,也让叙述性的报道更增戏剧张力,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至于催眠术在科幻小说的滥觞阶段即成为创作题材,原因或许就在于它同时符合“科”与“幻”的要素,兼具实验与陌生化的特征,如王德威所言:“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10] 更重要的理由是,催眠术提供当时的人们强国保种的“进化”想象。对应于新式出版物意图改造国体、启蒙群众的初衷,催眠术也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擘画出各种新的科学可能。从虚构出发,《新法螺先生谭》夸张地呈现灵魂与脑电能力的无远弗届,以此寄望黄种人从今而后能在各民族间扬眉吐气。[11]站在现实的角度,报刊杂志里各种标榜祛除恶癖、解决疾病、增进能力、扩大生产力的催眠术报道,则是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在现代转型阶段面临的难题,而催眠术无疑就是一组解答,指出人类进化的一条捷径。
“新式出版物的兴起让科学知识扩散的幅度、速度呈现惊人成长,然而它们所传递的终究只是文字与图像。
新式出版物的兴起让科学知识扩散的幅度、速度呈现惊人成长,然而它们所传递的终究只是文字与图像。如果单凭阅读的想象,缺乏现实生活中的眼见为凭,这些科学主题未必能够获得大众广泛的回响。展演活动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成为人们接触催眠术更切身的渠道,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民众都曾经观赏过一场又一场催眠表演,这些展演活动的预告或记录都清楚记载于当时的报纸中。
以《申报》为例,里头记载“寰球中国学生会”曾经数度举办催眠术表演会。[12]这个成立于上海的民间学生社团,是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留学教育的重要推手,办理过许多留外学者和政府要员的演说,内容涉及科学、医学、实业、时局等议题,足以见得催眠术在当时被认为具有相当教育价值。另外,南洋中学校友会、群学会、南洋路矿学校、青年会等团体也喜好在集会活动中聘人演示催眠术,而催眠术表演往往穿插在魔术、影戏、音乐之间,观赏人数从数十人到上千人都有。再者,催眠术也经常是赈灾慈善园游会、游艺会的热门节目,甚至租用戏院进行表演。常见的表演者除了中国人与日本人外,还有来自美国、法国、波兰、埃及与荷兰的“幻术团”“科学催眠曲艺团”或催眠专家前来巡回演出。有些表演的布置相当简洁,仅桌椅数张;有些则是超过10人的表演团队,结合声光、杂耍、野兽,令人目不暇给。
巡回杂技团在剧院里的售票演出有时只是借用“催眠术”的噱头,实则为魔术表演;[13]但其他许多本地的演示会却实际运用上了催眠的技术,并夹杂解说和表演、学理与奇观的成分,且不断有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要在这些展演中区分“学术”与“娱乐”并不容易。以下摘录一段表演的记述,或许能让我们稍微体会当时人们置身的表演场景:
夕阳西下,姚君乃登坛说法,历述催眠术之沿革及其功用,议论滔滔,如泻瀑布,如倾壶水,言词高妙,令人心折。俄而,作催眠术实地试验,欲施诸旁人之身,问座中孰来一试者?众皆畏怯不敢前。公推张君,张色变,频摇其手;又推王君,王亦然。于是余乃挺身而出。余既立于被催眠之地位,姚君命余坐则坐之,闭目则闭之。盖姚君谓予:被催眠者须精神贯注,一心一意,不可稍涉弗信之念,反是则损脑。余嗷然应之,弗敢违也。[14]
不难看出,伶俐的口才是表演者的必要条件,他们既要能掌握催眠术的知识,亦必须擅长塑造神秘、紧张的气氛,又要能在关键时刻让观众与被术者镇定安静、聚精会神。这些表演者为了吸引观众的观看欲望,也往往强调催眠术是西洋诸国与日本盛行的科学,而中国正值萌芽阶段,台下举目所见,尽为新奇。有些催眠教学书籍还会特别要求:“不论是在公众的或者私人的表演里,必须在开始的时候把这门学术做一个简短的说明”。也无怪,催眠术表演不只能吸引普通百姓围观,在传统戏曲、说书、杂技之外提供新的消遣选择,就连一些上层社会人士也会稍加驻足,例如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1880—1930),在他的日记中便曾记载自己“登天台看催眠术”,以及看电影戏中演出“以催眠术卧幼女空中”的剧情。
然而,观众有时抱着期待前来,最终却败兴而归。一些生意人打出催眠术的名号吸引观众购票,号称聘请日本催眠大师前来表演,实际上却是挂羊头卖狗肉。《申报》便曾报道一则宣传不实的案例,引发观众群情激愤:
苏垣庙堂巷畅园近日遍发传单,云聘请东洋催眠术大家,于九月一号开演,每人观费一角半。苏人皆不知催眠术是何等奇术,故是日往观者甚众,一时男女杂踏,拥挤不堪,皆延胫望其开幕。乃守至五句钟时,仍无所谓东洋技术,仅有一中国人出场,略做寻常戏法后,经园中经理人当众宣告:今日本园聘请之日本技术大家竟失信用,可否请诸君明日早降观看云云。众客闻之,大动公愤,咸云畅园设此骗术,哄人钱财,为众所不容,必须罚惩并勒令退回原价,一时喧嚷不已。[15]
在另外一些状况里,台上虽然表演的是催眠术,但表演者对催眠术半精不熟,空有派头架式却无法发挥效果。《兴华》杂志记载了一段失败的剧团实况:一名华人催眠术教授站立于舞台上,他穿着“洋式政治家与宣教士之礼服”,头戴如学院帽般的“方顶带穗之洋式冠”,征求台下自愿者。三个孩童被观众拱上台。不幸的是,其中两名孩童对催眠完全没有反应,被表演者赶下舞台。表演者用尽一切方法想要催眠剩下的那名男孩,但反应却未如预期。他不得已使出极激烈的声音及手势,意图加强催眠效果,结果反而造成男孩惊恐,更加不能入眠。最终整场表演在恼羞中收场。[16]这个失败表演的案例,一方面透露出催眠师的素质良莠不齐,徒有派头却学艺不精;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表演者如何在展演中操弄“西式服装”与“西式科学”间的表里对应——在公开的表演中,甚少表演者会选择身穿长袍马褂来示范这项技术。
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这些失败的表演经常被人当成骗术予以谴责,有时连观看表演的群众也一并被评论者视作愚民。大街上泛滥的催眠术表演,更成为某些号称催眠专业人士的眼中钉。他们斥责这些人是“跪在黄金偶像下的江湖催眠术者”,“用学术的名义以生财,或用牟利的伎俩来参加学术的运动”,对“文化的前途与学术的地位”造成极大妨碍。为了与一招半式的江湖术士划清界线,专业人士成立催眠学会,定期开办催眠讲习会,并建立起一套教学与考核的机制。在本书的第三章,将会有更多篇幅描写这些学会的策略。
不过,如果我们仅是将这些催眠术表演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催眠家的成功演出,另一类是冒牌催眠家的失败把戏,却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即使是受过训练的催眠师也必然承担催眠失败的风险,纵有精熟的知识,他们的催眠对象与施术环境仍都攸关演出的成败。将催眠术从日本引进中国的先驱者陶成章(1878—1912)就是一个明证。陶成章是光复会的成员,根据革命党人魏兰的记载,他在1905年赴日期间,“因中国人迷信最深,乃约陈大齐在东京学习催眠术,以为立会联络之信用,并著有《催眠术精义》一书”。[17]同年夏天,陶成章回到中国,在上海教育会通学所创先开设催眠术课程,讲授并示范催眠术。东海觉我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提到的“催眠术讲习会”极有可能就是陶成章所举办。可想而知,他的课程在当时受到不少关注,甚至学员的上课笔记还在《大陆》杂志上连载。[18]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代为发行的《催眠术讲义》,到了1918年已经印至第16版。[19]这份教材囊括西方催眠术发展史中的各个流派沿革、原理及应用方法,足见陶成章对此主题有一定的掌握。[20]
但即使像陶成章这样的先驱者,心中也经常挥之不去对催眠术失灵的担忧。知识上的真实性未必总能引导出实作上的确定性,但实作上偶然的失误却可能动摇人们对知识的信念。大众往往着迷于科学的万能和奇效,却未必考虑科学的条件性与不确定性。为了增加催眠术的成功几率,陶成章一度考虑借助药物的帮助。鲁迅记录下陶成章在此事上的彷徨: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催眠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
从鲁迅的描述可知,陶成章不容许表演失败是有理由的:舞台上的催眠术表演不单单只为了赚取观众的门票或打赏,其背后更包含招揽学员付费学习的长期商机,这份收入对落魄的革命分子格外重要。
我们可以借用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一词,看待上述催眠术展演的例子。 [21]从言说修辞、服装仪态到偶然性的控制,可以看到表演者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经营他们与观众的面对面互动。催眠术的科学形象成为塑造的焦点,用以满足观众的期待。然而,催眠术却不是催眠师的单人演出,他必须掌控跟被术者之间的默契,并寻求观众在态度上的合作,才能成功维系设定好的情境。至于在展演的后台,催眠师远没有台前的自信,他们担心失败,并深知一旦发生,科学形象将迅速瓦解。观众的无情或许来自他们的时代处境,身处在充斥前所未见的科技展示的城市中,各种新奇事物占据听觉与视觉,讯息之庞大和新颖使得大众再也没有权威得以依靠,亦无暇逐一深入分辨,唯有凭借当下的表面印象来决定他们的投资对象。![]()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光启书局
书名:科學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原作名: 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
出版年: 2021-11
页数: 289
定价: 78
装帧: 精装
ISBN: 9787208173385
[2] 例如,17世纪20年代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在《泰西人身说概》里将nerve翻译为“细筋”,并指出“细筋中无空处,止有气而无血,故身体不能觉、不能动者,因无气则无力也。”见邓玉函口授,毕拱辰编辑,《泰西人身说概》(1621),第131页。
[3]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52期(1999),第29—39页。更丰富的出版史研究参考: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收入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2007),第3—49页。
[4] Evelyn S.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p. 140. 罗友枝的研究容或有高估的问题,但若局限于口岸城市,高识字率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至于到民国初年,平均识字率到达30%以上也属相当合理。相关评估参考:张朋园,《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第455—462页。
[5] 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p.91.
[6] “Dr. Charcot and Hypnotism,”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7 May 1887, p.4.
[7] “Wonders of Hypnotism,”The China Mail,21 October 1887,p. 3.
[8] 《奥国心理学家杜吗博士在柏林动物院施催眠术于猴“彼得”》,《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20卷第26期(1936),第2页;《催眠术对于黑猩猩的效应》,《科学画报》,第4卷第8期(1936),第329页;《猩猩催眠术试验功成》,《知识画报》,第3期(1937),第33—34页;《猩猩之催眠:奥心理学家多玛之试验》,《新中华》,第5卷第3期(1937),第13—14页;《禽兽与催眠术》,《东方画刊》,第1卷第2期(1938),第24页。 [9] 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收入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第1—20页,特别是第5页。原收录于1905年6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新法螺》,该书共三篇小说,另外两篇为包天笑(1876—1973)翻译日本作家岩谷小波(1870—1933)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
[10]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2003),第330页。
[11] 关于徐念慈在创作上所提倡的进化想象,从《小说林》的发刊文章中即可见一斑:“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见东海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第4页。
[12] 《学生会今晚开会》,《申报》,1913年7月5日,第10版;《寰球学生会试验催眠术方法》,《申报》,1914年5月22日,第10版。
[13] 例如中国第一份以魔术为主题的杂志《幻术》,就曾载:“因幻术为高尚娱乐,简便易学;催眠近乎修养,深奥难能,岂可同日而语。幻术中有用催眠名词者,并非真的用催眠试术,以其状态宛如催眠,用以作为代名词耳。”见:《催眠神椅》,《幻术》,第1卷第7期(1932),第51页,收入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编,《民国珍稀短刊断刊:江苏卷》,第6册(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6)。
[14] 钱香如,《催眠术》,《申报》,1914年7月16日,第14版。
[15] 《催眠术骗钱小风潮》,《申报》,1913年9月4日,第6版。
[16] 《催眠术调查记》,《兴华》,第16卷第4期(1919),论说,第2—3页。这篇文章原本是以英文撰写,曾分别刊登在多份刊物上,包括《基督教出版界》(The China Bookman)、《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参考:The China Bookman,“Hypnotism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33(1919),pp. 80—81。 [17]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收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31页。
[18] 《催眠术讲义》,《大陆》(上海1902),第3卷第7期(1905),附录,第1—10页。
[19]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329页。
[20] 陶成章,《催眠术讲义》,收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16—322页。
[21] 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