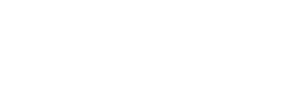美国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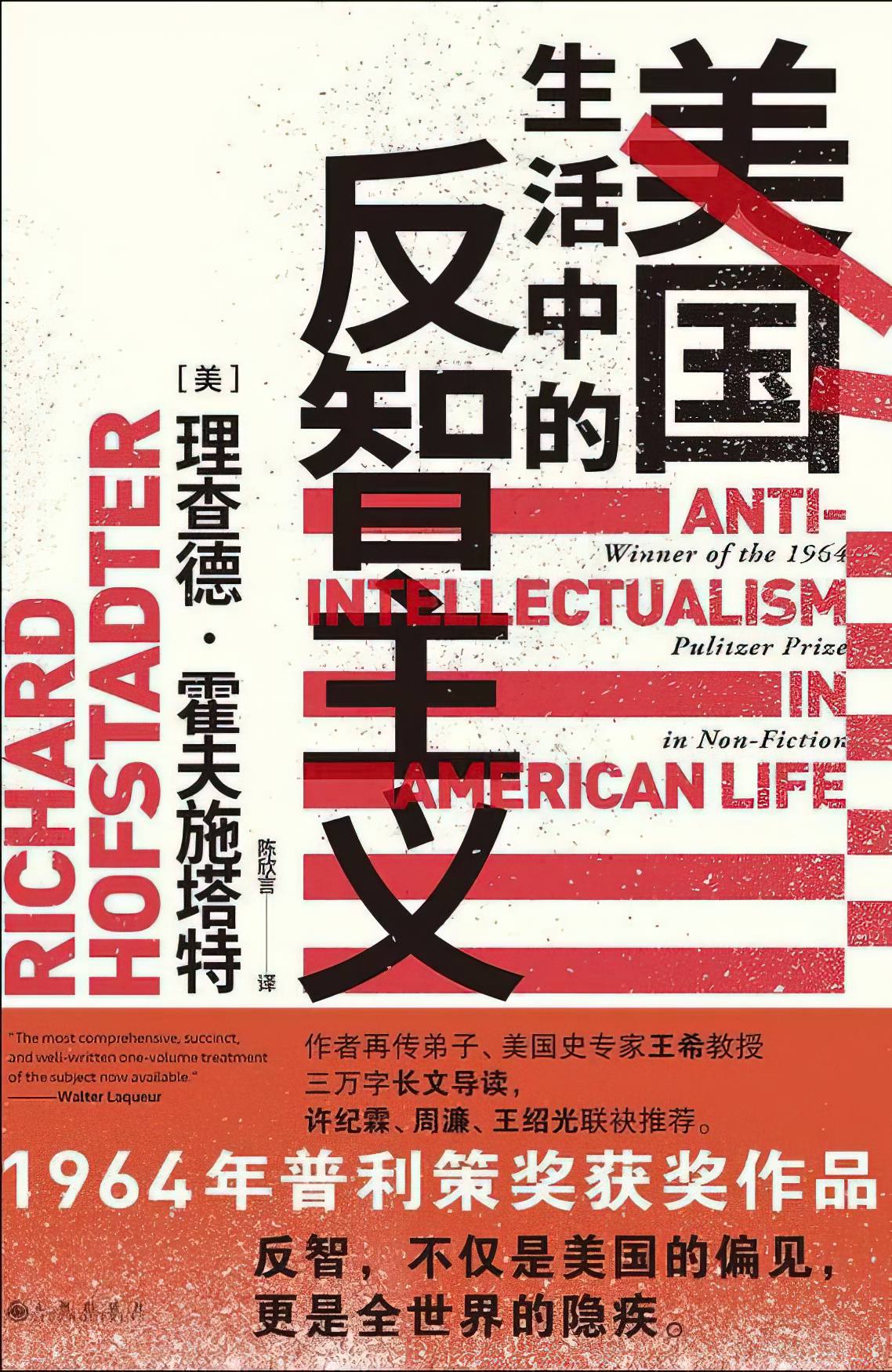
编辑:张弘 来源:燕京书评(微信公号ID:Pekingbooks)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的出版而变成了研究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概念,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影响。本文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和美国史研究路径为起点,叙述《反智主义》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与霍氏学术谱系的关系,通过对《反智主义》内容与观点的解析,延伸讨论“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力图揭示一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和“反智化”的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反智主义》)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当同代学者的作品大多被人遗忘的时候,该书的阅读价值却倍显珍贵。据悉,国内有数家出版社计划在2021年推出该书中文版。一书多译并同年出版,十分罕见。无独有偶,享有盛名的美利坚人文经典丛书2020年也推出了一部霍夫施塔特文集,排在首篇的便是《反智主义》。[2]
《反智主义》为何突然大热?除作者名气大和该书曾获普利策奖之外,近年来美国政治的乱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特朗普在4年执政中刮起一场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旋风,搅得美国和世界不得安宁。虽然他未能在2020年如愿以偿地获得连任,但仍然在1.5亿选民中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一些铁杆支持者更是在他的鼓动下,拒绝接受大选结果,攻击国会,这一切都令世人深感震惊。特朗普的言行举止粗暴鲁莽,治理国家更是漏洞百出,为何依然能够在总统竞选中做到一呼百应?除了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全球化对美国霸权形成冲击、两党政治撕裂选民等原因之外,美国选民本身是否也是“特朗普现象”的制造者?困扰当前美国的政治分裂和价值冲突是否有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心理原因?如果读者关心这些问题,阅读《反智主义》将会很有帮助。
事实上,《反智主义》并不直接讨论选举政治或分析选民的构成,但它讨论美国选民得以养成和建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具体讲,它讨论的是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一种“反智”(anti-intellectual)文化,其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人。霍夫施塔特将具有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称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他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反智主义”在美国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生活中的形成与演变做了详细的描述,揭示了“反智主义”如何广泛地渗透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动声色但持续不停地塑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霍夫施塔特的观察细致,研究扎实,叙述生动,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一些文字甚至可以一字不改地借用来描述当下的美国,而当代读者更能从他关于“反智主义”危害的警告中领悟到一种难得的先见之明。我想,这也许是中美出版界“重新发现”《反智主义》的动因所在。
诚如霍夫施塔特所说,《反智主义》是对20世纪中叶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尤其是对肆虐美国政坛长达4年(1950~1954)之久的“麦卡锡主义”—所做的一种回应,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反智主义”及其历史、“反智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知识分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等—却具有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含义。虽然霍夫施塔特自称这部著作不是“一部正规的历史学著作”(a formal history),而“更多的是一部个人作品”(largely a personal book),[3]但《反智主义》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的确代表了一种意义非凡的延续与创新。为了更好地读懂这部著作,理解它在今天的阅读意义,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此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它在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中所处的位置与意义。
霍夫施塔特于1916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Buffalo),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移民,母亲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他17岁入布法罗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在大学期间,他与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菲丽丝·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相识,在后者的影响下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并担任领导人的职务。1936年大学毕业后,霍夫施塔特与新婚妻子移居纽约市,先入法学院,但后来很快放弃,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美国史研究生。初到纽约的时候,霍夫施塔特夫妇与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来往密切。他们还前往南部乡村,调查黑人分成租佃农(sharecroppers)的生活状况,为霍夫施塔特的硕士论文收集研究材料。1938年,霍夫施塔特在《美国历史研究》(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第一篇论文,讨论关税与美国内战爆发的关系。同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研究生支部,但几个月后因不愿受党内斯大林式的思想控制而退出。与罗斯福新政时代的许多都市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年轻的霍夫斯塔特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积极寻求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他又十分崇尚自由主义的原则,坚决捍卫进行独立思考的立场。这两者构成了霍夫斯塔特早期意识形态的基础。194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美国思想史的奠基学者梅勒·柯蒂(Merle Curti)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读博期间,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兼职任教。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前往马里兰大学任教。1944年,霍夫施塔特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专著。1946年,他受聘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任教,从此终身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为伴。[4]
1970年,当年仅54岁的霍夫施塔特因白血病去世时,他已经成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26年的专著发表生涯中,霍夫施塔特一共出版了10部专著,包括《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4,此后简称《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此后简称《美国政治传统》)、《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1952)、《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发展》(1955)、《改革的时代:从布莱恩到罗斯福》(1955,此后简称《改革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与其他论文》(1965,此后简称《偏执风格》)、《进步主义历史学家》(1968)、《关于政党体制的思想:合法反对在美国的起源(1780-1840)》(1969)、《1750年的美利坚》(1971)。在他的10部专著中,《改革时代》获1956年历史类普利策奖,《反智主义》获1964年非虚构类写作普利策奖。此外,他还独自和与人合作编撰出版了13部美国史教科书、文献集和参考书,并发表了140多篇学术论文、书评和时事评论。与大多数史学同行相比,他始终拥有一个令人望尘莫及的、同时来自学术界内外的读者群。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55年修订后的销售量高达20万册(这对于任何史学博士论文而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的《美国政治传统》的销量更是一度高达100万册,并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种语言,至今仍为许多美国大学作为长期保留的经典书目。[5]
有人曾将霍夫施塔特的学术成功归因于他一生中遇到的几个“最好”(bests)——居住在美国“最好的城市”(纽约市),任教于“最好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最好的时刻”,为“最好的出版社”(Knopf),写作了“最好的著作”,并赢得了“最好的奖项”(普利策奖)。[6]此话只能部分当真。在某种意义上,霍夫施塔特不是一位“标准的”(standard)历史学家——他自己也承认不喜欢和不善于长年累月地做“档案馆里的老鼠”(为此他没少受同行的诟病)。但所有仔细而完整地读过霍夫施塔特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他的写作展示了三种能力:原创性的思想能力,对史料的想象和运用能力,超凡的文字能力。可以说,同时拥有这三种能力,是他获得巨大学术影响力的原因之一。霍夫施塔特将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视为自己研究历史的动力。他的每一部专著都涉及美国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进步时代的激进改革、学术自由、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进步主义史学、合法反对党制等。他对每个主题的研究都会产生一种开拓性的效果:或者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或者将既存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或者为未来的研究设定议程和方向。他的写作拥有自己的风格,潇洒不失优雅,生动不失严谨,犀利之中含有诙谐,“文史不分家”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读他的史学著作,读者能同时感受到充满哲学意味的启示、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力度和文学的典雅。正是通过他的写作,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地位革命”以及“反智主义”在内的一些原本只在学界使用的生涩名词和概念,变成了公共思想讨论中的常用概念,难怪后世学者称他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具有公共精神但保持低调的知识分子”(a public-spirited private intellectual)。[7]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时间跨度大,涉猎主题多,似乎难以按传统方法对他进行专业定位。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从他发表第一部专著起,他的写作始终贯穿着两种努力:一是探索一种新的、能够取代“进步主义史学家”(Progressive Historians)学派的美国史研究路径;二是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中的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有人称他是“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a historian of ideas),但他自认为是“研究政治的历史学家”(a political historian)。显然,他对“政治”的定义非常宽泛。1966年,在解释“政治”的概念时,他提到传统的“政治”研究关注的是“谁在何时、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什么利益”(who gets what, when, how)的问题,而他的“政治”研究关心的是“谁在感知和理解什么样的公共问题,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感知和理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感知和理解”(who perceives what public issues, in what way, and why)。换言之,人是“政治动物”,寻求和捍卫自身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处于政治中的人并不只是在寻求和索取各自的利益,而更是通过政治来表达和界定自己的“价值观、身份认同、恐惧与志向”。[8]如果我们将“政治”划分成“硬件”(国家机制、选举政治、法律、程序)和“软件”(选民、思想、价值观、情感)两个方面的话,霍夫施塔特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美国政治的“软件”内容,即处于政治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政治感情、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看来是“政治”研究的真问题。
霍夫施塔特的学术发展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并深受所处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和他自身学术追求的影响,包括《反智主义》在内的写作既是这个过程的产物,也见证了这个过程的发生。所谓“进步主义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主导美国史研究长达半个世纪,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等人。他们的写作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视为推动美国历史前进的动力。[9]霍夫施塔特在学术起步阶段深受进步主义史学的影响,在本科时代甚至视比尔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即便在与激进左翼政治脱离组织关系之后,他也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首先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霍夫施塔特在书中追溯了达尔文进化论如何在工业化时期的美国被改造成为推崇“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又如何在遭遇不同的批判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他尤其揭示了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如何摘取达尔文自然演进学说的观点,将之与斯宾塞的利己主义哲学、新英格兰清教伦理观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建构了镀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他非常敏锐地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原本是一种具有“激进”意义的科学学说,但在美国却为保守派所利用,并将之变成一种阻止激进社会变革、确保资本主义的“竞争”不受政府管制的思想武器。此刻,他已经注意到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划分的,而且“思想”与“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互动。他尤其注意到了他后来将在《反智主义》中展开讨论的一种现象,即当一种新的思想被“发明”出来时,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决定是否接受新思想时所采用的首要标准并不是思想本身的“真实与逻辑”(truth and logic),而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精神需要和先入为主的期盼”(intellectual needs and preconceptions)。霍夫施塔特的另一贡献是指出了思想在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当强调“达尔文式个人主义”的思想(Darwinian individualism)在美国国内受到左翼力量的挑战时,这种思想会利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机会,被转化成一种冠之以“民族利益”的“达尔文式集体主义”(Darwinian collectivism)思潮,为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正名。[10]《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霍夫施塔特在史学界的亮相之作,展示了他的史学识见和能力,但此刻他并没有挑战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前提。
与进步主义史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1948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中。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冷战进入高潮,美国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省美国历史上的改革传统。当时的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在罗斯福新政和“统一战线”政治的鼓舞下,希望借用进步主义史学的思路,创造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史学。霍夫施塔特则认为,左翼历史学家带有先入为主的立场预设,难以摆脱“偏见”,由此建构的美国历史并不真实,而且会继续造成一种美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以贯之的“二元对立”历史的认知误导。1945年,霍夫施塔特应克诺夫(Knopf)出版社之邀开始写作一些关于美国领袖和他们的思想的短篇论文。最初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左翼政治企图建构的新美国史观进行一种反思,希望寻求一种新的“左翼”解读来替代它。虽然这些短篇最终会结集出版,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建构“一种单一的关于美国政治或美国政治领导力的概括性理论”的计划。写作的过程并不顺畅,其间他经历了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的变故,若干篇章是他坐在妻子的病床旁边写成的。直到1948年写完书稿之后,他仍然不能确定如何找到将12个篇章连接起来的主题。[11]他研究的美国政治领袖包括了7位美国总统(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3位著名政治人物(奴隶制卫道士卡尔霍恩 [John C. Calhoun]、废奴主义者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以及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的严厉批评者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建国时代与工业化时期的两组政治人物。在人物选择和思想综述方面,除了文字有过人之处外,霍夫施塔特似乎并无标新立异之处。
随着交稿期限日益迫近,他最终迅速写作了一篇简短的(6页)前言,在其中提出了一种历史观察:尽管12个短篇覆盖的美国政治领袖人物的背景和经济立场不同,生活在不同的时段,但他们却分享一些“共同的”美国价值观,包括尊重私有财产,看重机会的价值,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鼓励在法治范围内对个人利益的争取。这些看似矛盾但得到普遍分享的“传统”正是美国作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秘诀所在,因为它们避免了让美国陷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漩涡之中。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思想中的共识”(the common climate of American opinion)的强调,直接挑战了比尔德等人提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也表明他企图在传统的冲突论和“二元对立”历史观之外识别和建立一套新的、为所有美国利益群体认同的价值观。[12]虽然霍夫斯塔特的原始意图更多是“祛魅”,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思想——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成才的英雄崇拜、资本主义的神话等——进行无情的剖析,但他批判的光芒完全为他强调的“共识”所遮掩。他希望在“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的路径之间寻求一种新的、更为独立的自由主义思路,但在冷战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背景下,他的著作很快被划归到“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的阵营之中,而共识学派因为宣扬“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成为了学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13]
尽管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政治传统》的出版将32岁的霍夫施塔特推到了美国史研究的前沿。这两部著作虽然主题不同,但在方法论上非常接近,都注重精英人物的思想研究,并关注思想的变化与不同思想的交锋。然而,真正为霍夫施塔特在同行中建立起不朽名声的是《改革时代》的写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霍夫施塔特从方法论、材料和分析手段上开辟了美国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片崭新的天地,也开启了他对“反智主义”问题的思考。
《改革时代》讨论的是19世纪后20世纪初的几场改革运动,包括平民党人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但重点放在平民党领导的农场主反叛和由都市中产阶级发起的进步运动上。这一段历史是进步主义史学的起点,许多结论长期主导了历史学界的解释。霍夫施塔特运用心理分析、社会功能解析等方法,对平民党-进步运动及其参与者进行重新解读。与先前著作不同的是,他将研究重点放在改革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和中下层领袖人物身上,观察和分析他们的世界观,解读他们使用的抗议方式和语言。霍夫施塔特正面质疑了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利益冲突的观点,认为平民党人的反叛并非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乡村商人阶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由此产生的愤怒所致。在他看来,身处19世纪后期工业化时代的西部和南部自耕农人群具有一种“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一方面他们梦想回到想象中的传统农业社会、享受大众民主的平等参与;另一方面又竭力希望改进农业技术,使用商业手段,通过施压政治来增加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影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业经济的比重和重要性降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失败边缘的农场主人口于是祭出民粹式民主的大旗,要求改革州与联邦政治,打击工业和垄断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卷入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新富阶层的崛起引发了各种新旧中产阶级群体的不满与恐惧,“地位巨变”(status upheaval)——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域中产生大量的地位“焦虑”,正是这些集合起来的焦虑构成了进步时代的“改革冲动”。霍夫施塔特指出,平民党人反叛者并没有真正考虑工业无产阶级、移民劳工和都市无产者的利益,而是借助美国历史上的仇外、反犹和种族主义文化来宣泄不满和组织抗议;而进步主义者所推动的也并非完全是一种进步主义,而是同时带有落后思想而充满偏见的地方保守主义。霍夫施塔特观察到,人们通常将平民党人——进步运动视为罗斯福新政的前奏,其实先前改革的动力带有大量的负面内容,包括孤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对欧洲和欧洲人的仇视,对不同种族、宗教和出生地的人的惧怕,对大商业、工会、知识分子和东部生活方式的反感等。这些负面的动力为新政前后的保守主义势力——包括反移民、三K党、禁酒运动、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的崛起做了铺垫。所以,改革并非是一条从落后走向进步的直线运动,“推动昨日改革背后的动力,既可以为今日的改革所用,也可以为今日的反改革力量所用”。[14]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时代》代表了霍夫施塔特与进步主义史学的决裂。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属于“共识学派”,而且他对保守主义始终抱有一种反感,但他对阶级冲突的否定和对共享美国价值观的强调,无疑加深了外界对他的“误解”。他在《改革时代》中使用的方法也招致了包括新左派历史学家在内的批评。事实上,霍夫施塔特并不是盲目地推崇“共识价值”,而是想摆脱经济冲突论这种在他看来过于简单和僵化的历史解释的羁绊,希望探讨导致历史变化的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力量所在。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美国政治传统》再到《改革时代》,他的研究一直没有脱离过这种努力。与此同时,《改革时代》的写作也促使他去思考所谓“共享的”美国思想、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内涵、形成与传播,并给予这些思想的建构者——平民党人、进步主义者、在“地位革命”中丧失了特权和声望的小镇和乡村政客,以及那些游离在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之外的“独立派”精英分子(Mugwumps)等—特别的关注。他注意到,这些人是真正的基层美国思想的建构者,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民主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大众暴政”意味的民意,支持或阻止美国社会的改革。[15]此刻他已经开始将历史上的大众民主与“反智主义”联系起来。
《改革时代》出版时,美国政坛上的“麦卡锡主义”闹剧刚落幕不久。从1950至1954年,共和党新科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借冷战的反共潮流,声称要清洗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学、媒体、艺术界、公民组织以及工会中的亲共分子,并利用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国会主导了一部反共闹剧。他绕开司法程序,任意传唤嫌疑人,并利用人身攻击、随意指控等手段,对美国左翼力量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威胁。麦卡锡主义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它所制造的国内恐怖政治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感震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52年、1956年两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连续两次被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击败。在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眼中,两人的政治对决是新政自由主义与反新政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决,更是一场理性政治与反智主义政治之间的对决。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史蒂文森的失败,说明“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政治中占了上风,美国知识分子也因此面临一种“世界末日的劫难” 。[16]
1954年麦卡锡受到参议院的惩戒倒台之后,美国学界和思想界开始检讨美国为何会出现“麦卡锡主义”。最初的讨论集中在冷战时代国家安全与公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的关系上,尔后逐渐延伸至对“反智主义”的检讨。[17] 1954年12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柯蒂(霍夫施塔特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第一次深入地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问题。柯蒂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批判、实验和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的作用,但大众却对他们抱有一种“怀疑(suspicion)、反对(opposition)或贬损(derogation)”的态度;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与反感由来已久,其形成受到相关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包括教派之争、边疆文化、实用主义、大众民主以及对自我造就的文化英雄的推崇等。柯蒂指出,当代反智主义却是源于冷战政治,麦卡锡主义以“一种凶狠恶毒的特殊形式”,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压制,将美国带入“一个非理性和令人焦虑的时代”,不仅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将他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工具”,而且威胁到了美国文明的健康发展。[18]
柯蒂的演讲于1955年1月发表,《社会问题期刊》随后组织了一场笔谈,邀请8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笔谈主持者将麦卡锡界定为“当今美国最显赫的反智主义者”,将反智主义界定为“一种极为宽泛的社会态度或价值观”,其特征是反对“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来指导和控制(社会)变革”。参加笔谈的历史学家威廉·洛伊希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同样认为北美的历史环境孕育了反智主义的文化,并指出,当代反智主义的高涨与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得重要有关。[19]1959年,著名政治评论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进一步指出,保守主义力量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反共为借口,根本目标是摧毁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后者力量的不断壮大令他们感到恐惧。[20]
这些讨论显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两场“冷战”:一场是美国在国际上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冷战;另外一场是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焦点是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在霍夫施塔特这一代人看来,“极权主义”不光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昭示了这种可能。
霍夫施塔特没有参加笔谈,但他比柯蒂和其他人更早地关注和讨论了“反智主义”现象。1953年当麦卡锡主义进入高潮的时刻,他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讨论了“反智主义”的问题。[21]当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去智识化”危机——大学教师的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管理权掌握在外行手中,教授的自治权可以被“董事会任意合法地收回”,课程设置中充斥着大量的技能训练,无法培养出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人等。他将高等教育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人对“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的迷信。在他看来,这种形式的民主貌似追求“平等”,实际上却是一种受肤浅的大众情绪支配的政府形式,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通过对现代媒体的操纵,制造出草根“暴政”,以此恐吓知识分子,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不仅听由民粹主义政客摆布,而且还将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视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恶人。[22]
柯蒂、洛伊希滕堡、李普塞特以及其他人在同一时段对反智主义的讨论,对霍夫施塔特的思考无疑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柯蒂的演讲。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柯蒂1955年的演讲与霍夫施塔特的《反智主义》,可以看到两者在主题上的重叠。尽管如此,《反智主义》不是对他人观点的简单重复或扩展,而是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下利用丰厚的史料支持,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所做的全面检讨和分析。霍夫施塔特认为,虽然反智主义很少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但反智主义的影响却无孔不入,渗透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兴起和泛滥,原因之一是美国提供了适合它生长的政治和文化土壤。[23]
什么是“反智主义”?这是霍夫施塔特在《反智主义》书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思想的轻蔑”(disrespect for mind),但它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ism),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attitude),即一种由“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a complex of traits),其共同特征就是对“知性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和那些奉行“知性生活”的人抱有反感与怀疑,并始终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24]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霍夫施塔特在第一章里列举了十数种“反智主义”现象,其范围从民间对学究式人物的嘲讽,延伸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知识分子的反感、麦卡锡对国务院专家的攻击和右翼势力对大学教授和专家的抨击等。他同时指出,反智主义并非一定是一种“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而且反智主义的领袖人物,甚至会是一些“深切关怀思想的人”。他们既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那些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的群体——如三K党和美国共产党、资本家和工会领袖等——可能同样分享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仇视。为此,“反智”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美国态度,并不只限于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且“反智主义”也不是一种天生的邪恶力量,它实际上与许多“善业”(good causes)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如此长久地深入人心,渗透在美国社会与生活中,所以反智主义的批评者需要将它“与它赖以生存的仁慈冲动分离开来”。[25]
那“反智主义”的对立面——“智识”(intellectualism)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intellect)——又应该如何界定呢?什么是“智识”?谁是“知识分子”?柯蒂在1954年的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包容性宽泛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的“知识人”(man of knowledge)到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者所称的“脑力劳动者”(brainworkers),再到当下的原创性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在大学里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等,都可以被包括在内。[26]
霍夫施塔特则不这样认为。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加严格。在1953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将“知识分子”生动地界定为那些“在晚餐之后大脑(mind)很可能继续处在活跃状态之中的人”。[27]在《反智主义》中,他则指出,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现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标准,即便在学术界,也并非人人都能够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霍夫施塔特的眼中,“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某些作家”以及大学里的许多教授都不能算做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是“以理念为生,而不是为理念而生”。所以,理智生活、怀疑与批判精神、对思想的崇尚、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智识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为了说明他的观点,霍夫斯塔特特意对“聪明人”(a man of intelligence)和“知识分子”(a man of intellect)做了对比和区分:聪明人心灵手巧、悟性极高,而知识分子不仅具有领悟力,而且更能做理性思考;聪明人使用现实手段解决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则具有批判能力,并善于做创造性思考;聪明人关注部分和眼下,知识分子则思考全局和未来。[28]霍夫施塔特还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的一些特质——他们拥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curiosity)、醉心于智识工作的“玩兴”(playfulness)和追求真理的“虔诚”感(piety),但他们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以集体的方式扮演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触角”(moral antennae)的角色。他们在公众尚未意识到之前就考虑和提出社会需要关切的基本道德问题,所以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价值观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他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掌握政权或独霸真理,而始终是在“对新的不确定性的追寻”之中。[29]
基于这种对“反智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界定,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的起因做了探讨。他认为,在当代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现代十字军式的讨伐中, “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只是工具”;保守主义真正希望惩罚的不是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影响,而是来自美国本土的新政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因为后者比外来的激进主义更具有威胁性。[30]他借助在《改革时代》一书中使用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对当代“反智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反智主义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包括对新政的憎恨、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对教会现代化的反感以及对福利国家和联邦经济管制的反感等,起源于对现代美国的恐惧和对逝去美国的怀念。在此,他几乎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者等同于19世纪末期的平民党人,认为前者分享了后者曾经有过的政治心理状态,把即将逝去的美国看成是一个理想世界,因为它拥有孤立主义带来的安全、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舒适、新教主导的文化传统和蓬勃生长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当代的保守派对新政以来的现代美国抱有一种真实的恐惧感,为了捍卫昔日的旧梦,不惜拥抱各种阴谋论,集合在“反智主义”的旗帜下,与罗斯福新政顽强地进行着一场“地下反叛” (an underground revolt),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绝妙的渲泄和爆发的机会。
在这里,霍夫施塔特还讨论了一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的国际原因,即外来思想的“侵入”。如果说外来思想的早期侵入是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卷入国际事务的结果,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美国积极主义”(American activism)则为更多新的外来挑战打开了大门。美国人原以为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美国思想的影响下“会放弃……意识形态,接受我们的民主形式,并将之运用来……努力追求幸福”,没有想到曾经崇尚美国的其他人民会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传统,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形式的外来挑战的准备,因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夫施塔特用他风格独特的犀利语言写道,“美国人在享受因他们的激励而带来的胜利的同时,也在吞下激励所带来的失败的苦果。”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国内保守派非但不明白美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反而将美国面临的困境怪罪于国内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的无能与腐败的无情批判,从而将知识分子当成替罪羊,置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对立面。在霍夫斯塔特看来,保守派建立的这套“虚构的和完全抽象的对立状态”(a set of fictional and wholly abstract antagonisms)不仅将知识分子妖魔化了,而且将“爱国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揉合在一起,将美国人推向一种“虚构世界”(mythology)之中,致使整个社会无法进行关于真相的常识性讨论。[31]这在他看来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所在。
为了梳理“根植于我们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选取了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这四个领域作为“美国生活”的主要侧面。虽然他没有解释为何选择这几个领域,但不难想见它们与美国人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和“智识”世界。
在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将宗教列在第一位,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宗教似乎与“反智主义”的关联不大。但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却显示,殖民地和早期美国的宗教教派之争正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源头之一。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缺乏欧洲王权国家中的统一宗教建制。虽然早期的清教教士在新英格兰地区构成了一个“有学识的、能写会道的”智识阶层,还建立了哈佛学院,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对浸信会、贵格派等异教教派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容忍。[32]教派冲突在18世纪上半叶第一次“大觉醒”时达到一个高潮,而殖民地的扩展和经济生活的多元化更推动“正统”教派迅速走向衰落,以福音派为基础的奋兴派牧师(revivalists)乘机取代了传统的“智识派”教士。奋兴教派的布道者出身普通,自学成才,利用感性色彩极浓的布道方式将被传统“正统”教会排斥在外的信众吸引过来。到美国革命发生之时,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激化了教派之争,导致了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产生,新教教会的形式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种“自愿性组织”,对所有人开放,无须在教会或牧师面前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感。到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觉醒”发生时,宗教多元化和自由化已经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特征,早期宗教中的“智识”阶层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33] 19世纪的教会为扩大规模,赢得教友的忠诚,奋兴主义者提倡对“普通人”(simple people)用“简单思想”(simple ideas)布道,抛弃了传统教士对教义的智识讨论;牧师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解释者,而被降低为宗教社团的司职人员。[34]与此同时,福音派借助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深入新开发的西部和新兴的城市,利用市场革命产生的商业化机制来普及宗教皈依活动。类如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这样的新派布道师也采用适合普通民众的布道方式,将《圣经》故事与小镇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赢得信众的狂热吹捧,但这样做也加速了宗教领域的“去智识化”。[35]
然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国家内部流动性的增加,奋兴主义教派也遭遇了世俗力量的挑战并产生了内部分裂。20世纪20年代,奋兴主义教派力图捍卫自己在美国的宗教地位和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影响力,与不同的世俗改革力量围绕达尔文进化论和理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科学与神学的对决中,由乡村和小镇民众组成的传统美国发起了一系列对现代美国的抵制,包括第二波三K党运动、禁酒运动、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以及1928年总统大选等。但这种“对现代性的反叛”最终是徒劳的,反而帮助建构了新的都市政治力量,最终为罗斯福新政的来临准备了选民基础。[36]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初福音派宗教势力反对现代性情形的描述,非常生动,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人想起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相关情形。但霍夫施塔特的用心在于说明宗教保守主义与麦卡锡反共主义之间的精神联姻。换言之,宗教保守主义之所以成为美国反共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它将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信仰体制,至于美国是否真的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或共产党人是否真的在美国存在并不要紧,所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设定中,所有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也就被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为“一场精神决斗”(a spiritual Armageddon),宗教情感深厚的美国人也因此被带入一种走火入魔的反智主义陷阱之中。[37]
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草根派取代精英派的过程。在霍夫施塔特眼中,美国建国者一代人可被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富有学识,推崇理性,崇尚科学。这个“贵族精英”(patrician elite)群体不仅创建了美国的政治体制,而且还成为了第一代领导人,所以早期的美国政治是一种“绅士政治”。但随着政党政治在19世纪初的兴起,“大众民主”(a popular democracy)取代了精英政治,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在激发其支持者参与政党政治的同时,也赋予他们抨击精英政治、反对地位差别的勇气。[38]在1828年总统大选中,拥有哈佛学位、崇尚欧洲文明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被出身寒微、行为鲁莽、靠战场军功出名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击败,早期的精英政治就此谢幕,让位于延续至今的“大众民主”。随之而来的“杰克逊民主”将分赃制(获胜政党独享公职任命权)、公职轮回制(政府公职不由固定的精英阶层担任)和恩惠制(政党根据党工忠诚程度分配利益和官职)等带入美国政治之中,在体现“民主”的同时也强化了“反智主义”;政府成为了一种由政党控制的、必须分享的公共财产,而企图保持独立的知识精英则被排除在政党体制之外,失去了与“反智主义者”抗衡的平台。[39]重建时代不愿与两大政党为伍的“独立派”企图恢复新英格兰文化传统和清教伦理,推动联邦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痛斥政党腐败,但在对手使出的“平等主义情感、政治机器的贪欲以及反智主义”的杀手锏面前,他们毫无招架之力,还被对手耻笑为是女人气十足的遗老遗少。[40]
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政治是在20世纪开启之后,但此刻的“知识分子”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旧式“知识精英”为新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所代替,而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管理的复杂性也要求政府借助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的帮助。进步时代担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对知识分子也多少抱有同情之心,但“知识分子”最终进入到政府之中并受到重用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时代。虽然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能够成为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并能对掌握实权的人施加“一种广泛而关键的影响力”(a pervasive and influential influence),已经是知识分子所取得的巨大政治进步。[41]然而,他们对政府权力的参与也刺激了新一轮反智主义的兴起。保守派将知识分子变成了美国失败的替罪羊,选民中的“反智主义”与反精英的平等崇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打击知识精英的“民主”力量。在1952年、1956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大胜史蒂文森,近乎于复制了1828年杰克逊战胜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一幕。尽管不喜欢知识分子,艾森豪威尔和保守派共和党人却没有抛弃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霍夫施塔特认为,当现代美国社会的治理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尖锐和充满矛盾的问题”(an acute and paradoxical problem)。[42]
在“实用性文化”(The Practical Culture)的标题下,霍夫施塔特讨论了美国商业、商业文化以及相关领域中的“反智主义”的历史发展。“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出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柯立芝之口,但自殖民地时代起,商业与商业文化就一直是美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历史上,商人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反感和敌视的紧张关系之中,但两者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商业活动是美国经济的主干,由此产生的商业行为和心理习惯影响着大多数人对待文明和宗教的态度。边疆生活的经验和商业竞争的需要,使美国人养成了做事讲求实用、相信直接的经验、反对空谈或抽象思辨的行为习惯,而政治上的“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则始终赋予美国人“一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在大众文化中,自我造就的成功者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致富者是美国人的文化英雄。即便是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物,也反映出实用主义文化的重要——学究气十足的汤姆·索耶(Tom Sawyer)代表着“智识”文化的不现实性,灵活机智的哈克贝利·芬(Huckleberry Finn)因善于处理现实问题而被视为土生土长的美利坚智慧的象征。[43]
随着商业主导了19世纪的美国生活,对凭自力更生(self-help)而发家致富者的推崇便成为一种民间文化,实用性也成为美国教育的宗旨。公立教育中的人文课程不仅被认为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而且还被认为是在误导学生养成不必要的雅兴。虽然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商业成功与商学院的训练挂钩,但商业界对学术界的传统怀疑依旧存在。[44]早期的农场主人口中还有一些受过教育、致力于鼓吹农业技术的绅士农场主,但现代的底层农场主对子女接受大学教育并不热心。在这一部分中,霍夫施塔特还考察了工运和激进运动中的“反智主义”。他注意到,激进知识分子与劳工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工会视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而行业工会本身希望追求的经济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扩大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利益分享,两者在政治宗旨上并不投缘。此外,为赢得工会的信任,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身段,“在思想上去阶级化”(declass themselves spiritually),这样做实际上导致了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异化”。美国共产党这样的激进组织更是具有“反智主义”的特征,因为它坚持单一的意识形态,不容任何思想异见,这一切令知识分子在其中难以立足(在论述最后一个观点时,霍夫施塔特除了列举许多左翼美国作家在20世纪30、40年代脱离美共的例子之外,也一定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与美共短暂交往的经历)。[45]
霍夫施塔特讨论的第四个美国生活侧面,是美国的公立教育。在1953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已经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反智主义”提出了批评和警告。在《反智主义》一书中,他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公立学校的师资、管理、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等问题上。霍夫施塔特认为,建国者一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教育与共和国存亡的关系,因而十分重视建立国民教育体制。然而,19世纪的美国公立教育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一直在一种“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低廉的教师待遇、破败的校舍、“去智识化的课程设置”(de-intellectualized curricula),以及对拥有优秀资质的学生的忽视等。与高等教育一样,因为受到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影响,公立学校的运作一直为地方政治所控制,教师素质不高,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心智”(mind)的训练和培养。在讲求“平等”和“民主”的环境下,美国教育的管理者和改革者拒绝把教育视为一种培育“上流文化”(a high culture)的过程,而始终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将教育的目的设定为培养“诚实、勤奋、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有用公民,以教会学生实用的生活和专业技能、扩展他们的“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ies)为目标。这种耗时长、低水平、低要求的公立教育,对于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和具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因为前者需要及早进入就业市场,后者需要及早进入大学深造)。[46]
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将高中变成了美国中学强制性教育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在古典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竞争中,后者取胜。所谓“生活适应”(life-adjustment)教育的课程设置被引入,以加强学生的生活技能训练。这种将中学教育与为大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脱钩的做法,极大地降低了公立教育中的“智识”内容。此外,教育的标准不是提倡优秀,而是讲究平等,向能力弱的学生看齐。霍夫施塔特认为,这种新型教育表面上看是民主、激进的,但实际上却是保守、落后的,极大地助长了中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智主义”;注重平等的教育实际上催生了美国教育的平庸,致使其在智识训练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和苏联。[47]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专辟一章来讨论美国教育改革的领袖人物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杜威的原意是希望学生使用心智(mind)作为工具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强调智识与行动能力的“双重并进”,从而在一个与现实接近的环境中将儿童教育改造为一种“社会重构的主要力量”。杜威从来没有提倡过“无方向的教育”,但他也未能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实用标准,所以最终没有解决培养学生的标准和方向的问题。霍夫施塔特对中小学教育的最大批评是,教学改革在强调民主和平等的同时,降低了对智识能力的训练,打击了优秀学生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就的志向与勇气。其结果是,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很容易成为“顺从”文化的俘虏。[48]

在讨论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四个领域的演进和表现之后,霍夫施塔特用结语一章来讨论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疏离”(alienation)与“顺从”( conformity)困境。他注意到,在现代反智主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不但不进行反击,反而力图重新“拥抱国家”,与主流社会重归于好。这种在他看来是向保守主义势力投降的做法似乎有情可原,[49]因为美国知识分子从未作为一个强大而稳固的群体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殖民地时代的清教教士和革命时期的建国者也许是美国最早的一代“知识分子”,但他们很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19世纪后期的“独立派”虽然继承了建国者的精神遗风,但他们与权力不沾边,并且与时代脱节,不成气候。此外,在20世纪之前,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在美国从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有内在认同的阶层存在过。“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没有机会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直到19世纪90年代,当“知识分子”的概念从法国进入美国的词汇之后,美国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形成认同,成为“一个内部更有凝聚力的阶级” (a more cohesive class)。随着知识分子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改革运动的参与,他们的立场也从进步时代的“中间偏左”逐步转向大萧条和新政时代的“更左”方向。尽管知识分子分享左翼和激进改革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要面对来自左右翼的反智主义传统,而后者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民主体制和平等主义的情感”(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egalitarian sentiments)之中。所以,知识分子始终面临一种身份认同的困难——一方面他们力图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员,希望为更大的公众利益而战;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民主社会”中的各种粗俗主义。不管他们是否承认,知识分子都是一个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强调思想的独立、理智的生活和拥有批评的自由。这一切都会与主张“民主”和“平等”、反特权、反精英的大众构成一种紧张关系。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在改革的高潮中可能会被掩饰,但当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知识分子会很便利地变成反智主义的牺牲品。[50]在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美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美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是一个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问题,但在霍夫施塔特写作的时候变得格外重要。当知识分子的身份在20世纪初从旧时的“有闲阶级”转化成为新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之后,他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获得了经济安全,进入到了政府的权力结构中,重要性和地位都得到了承认。但这种政府权力与知识分子“和解”也可能知识分子堕落的开始。获得了机会和利益的知识分子会被权力“微妙地腐蚀”掉,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进入权力体制的知识分子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敢批评美国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也不敢批判“美国政治话语的愚蠢”。[51]霍夫施塔特意识到,学者(scholars)的工作需要大学、研究所甚至政府的支持,但这一切支持都会对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和立场的独立性提出挑战。然而,知识与权力的地位并不平等——为权力服务的知识最终会变成权力的一种工具——所以,“知识”与“权力”既不能“脱钩”(divorce),也无法“联姻”(union)。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呢?霍夫施塔特开出的药方是,保持知识分子的多元化和智识生活的多样化。他警告说:“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只是服务于权力,如果所有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们与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有任何关联,并且认为他们的责任必然而且也只能是为权力服务的时候,事情就会出现悲剧性的后果”。尽管如此,霍夫施塔特仍然对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继续幸存抱有希望。他在全书结束时表示:只要个人意志仍然能够保证在“历史的天平”上占有一席之地,知识分子和智识主义就不会消亡。[52]
《反智主义》的写作代表了霍夫施塔特学术生涯中一次非同寻常的努力。他以“反智主义”为核心范畴,使用数量和种类上都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材料,展示了美国宗教、政治、经济和教育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反智主义”以及它们的延续与变异,从而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美国历史叙事,为读者开辟了一种解读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视角。我相信,这个视角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看到隐藏在“民主”“平等”这些较为耳熟能详的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政治实践之下的另外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美国历史和文化,从而获取一种对目前美国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更深刻、更有历史感的认识。与此同时,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的概念带入我们的词汇中,帮助我们发现、认识和反思中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并比较不同政治文化中是否会产生同样性质的、具有同等危害的“反智主义”。
也许,《反智主义》带来的最大启示是为我们呈现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无解悖论:即一个立志追求和维系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体制,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制造一种“反智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霍夫施塔特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悖论对美国文明始终是一种威胁。一旦大多数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反智主义”的生活方式,“反智主义”的情绪与心态就可能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并在特殊的政治时刻,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将其放大并转换成一种貌似“民主”而实为“暴政”的力量,最终扼杀拒绝顺应大众潮流的人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一个拒绝批判并扼杀了批判者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社会。
霍夫施塔特的担心——思想自由在民主社会中遭到扼杀——并不是危言耸听。他从冷战时代保守主义的喧嚣和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政治恐怖中看到了这种危险。事实上,在写作《反智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对“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的政治在美国政坛上的再度出现发出警告。1964年,就在《反智主义》获普利策奖的同时,霍夫施塔特在《哈珀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以“反智主义”为基础的“偏执风格”政治。他将“偏执风格”的政治视为一种由非理性思维和非理智行为主导的政治,其特征是先入为主,拒绝真相,夸大事实,将一切与自己信仰相悖的人与事都与阴谋论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麦卡锡的成功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美国民众在冷战时代的焦虑感——因担心自己、家庭、社区和国家的传统优势地位丧失而引发的焦虑——并通过现代媒体和党争提供的政治空间,将大众焦虑转化成为一种恐惧,进而将这种恐惧放大,大到迫使普通美国人在政治上拒绝共产主义、在道德和心理上将共产主义视为妖魔鬼怪、将一切事实上的或想象中的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视为敌人的程度。[53]
如果霍夫施塔特活到今天,我们不难想象他会如何解释“特朗普现象”。他的《反智主义》已经对“反智主义”的泛滥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勾画了有力的暗示。冷战之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9·11”恐怖主义袭击摧毁了美国人传统的地理安全感,全球化和数据化加速了知识的更新和信息的分享,极大地刺激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成长,而后者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格局。后发国家抓住这些新的优势,直追美国,美国作为“最富有、最自由、最伟大”的国家的地位不保,曾令美国人骄傲不已的“上帝选民”和“天定命运”的神话不堪一击。这一切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现实。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拯救美国的政治领袖的出现,而他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于许多支持者来说是一个熟悉的、似乎触手可及的美好旧梦。[54]21世纪的特朗普支持者们也分享着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的焦虑与愤怒:他们希望找回父辈曾经享有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心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他们怀抱对“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天然反感,拒绝接受任何“非美”(un-American)的思想与实践,并将反智主义美国的未来寄托在特朗普的大选获胜之上。
“《反智主义》为我们呈现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无解悖论:即一个看似立志追求和维系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体制,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制造一种“反智主义”的生活方式。
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反智主义》也将“反智主义”的概念带出学术界之外,使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使用的分析概念。但在方法论上,《反智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霍夫施塔特的写作带有明显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目的——为了现实批判的需要,采用现代思想路径或价值判断来诠释过去。他建构了“反智主义”概念,以此来设定研究路径,寻找相关材料,建构叙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令人质疑“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霍夫施塔特列举了不同生活领域的“反智主义”,但并没有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本质上的分析。殖民地时代宗派主义中的“反智主义”与杰克逊民主时代的“反智主义”是同一种类的吗?如果说“反智主义”的通用特征是“对思想的蔑视”,那“思想”(mind)应该如何界定呢?哪一种“思想”才算是“理性的”,应该受到尊重?霍夫施塔特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霍夫施塔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也非常宽泛,甚至有些随意。霍夫施塔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了各种人物:殖民地时代的清教教士、美国建国时代的领袖人物、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政党政治时代的“独立派”、进步时代的“专家”、罗斯福新政的“智囊团”成员,以及麦卡锡时代敢于批评美国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等。这些人背景复杂,成分多元,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而他们的反对者是“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呢?霍夫施塔特没有解释。事实上,正如他在《反智主义》的“结论”中所指出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稳固的、独立的、可以清楚识别的群体,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一种一以贯之、具有传承基因的“思想”体系。相反,我们从霍夫施塔特的描述中更多地看到的是美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完整性和多元性。因此,当我们看到他采用这种“知识分子针对反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v. Anti-intellectual)的思想模式来建构他的历史叙事时,不免想到他是否同样陷入了他力图批评的进步主义史学曾有过的局限性。如同利益冲突决定论一样,霍夫施塔特的二元对立模式也同样限制了我们去认识“反智主义”和“智识主义”各自的内部复杂性。譬如,所谓的“反智主义者”中会不会也有“智识主义”的成分呢?而所谓“智识主义者”(包括知识分子本身)是否也可能是“反智”的呢?
《反智主义》最容易为人诟病的是它隐含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当“智识”作为一种衡量标准时,拥有智识能力或选择过理智生活会被认为是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素质。虽然霍夫施塔特强调知识分子本身有很多的缺点,但因为智识生活更为理性,因此它比反智生活也更为优越。然而,霍夫施塔特并没有解释“智识”与“反智”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两者是否会发生转换。这种“精英主义”立场最终也将使霍夫施塔特陷入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反智主义》与其说是对“反智主义”的批判,不如说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处的恶劣环境的抗议与哀叹。《反智主义》的“结语”似乎是一首为理想状态的自由主义送终的哀歌。一方面,“反智主义”正在加速演变成为一种右翼势力的“偏执政治”,另一方面,左翼政治也在变得更加“激进”。那些力图在“左”“右”政治中间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包括霍夫施塔特本人——发现自己能够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的听众与读者也在迅速分流,“独立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批判力量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难以抵挡左右翼政治的夹攻。自从20世纪30年代末脱离左翼政治的组织和活动之后,霍夫施塔特一直埋头于象牙塔中(准确地说,他一直埋头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哈密尔顿楼六层的办公室中),力图在左右翼政治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自由主义立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与反对越战的抗议浪潮席卷整个美国、左右政治力量的交锋日趋白热化,他发现继续坚持政治“中立”愈加困难。1965年,霍夫施塔特与其他著名的历史学家一起,参加了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举行的第三次“塞尔玛进军”(Selma March)抗议活动,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民权运动的直接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发起第一次“塞尔玛进军”的是黑人学生领袖约翰·路易斯 [John Lewis,他在民权运动后当选并担任国会众议员多年],当时他为了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州警的暴力,在书包里放了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55]尽管霍夫施塔特在感情上同情民权运动,也坚决反对越战,但他很少直接卷入到左翼抗议活动中去。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为反对越战和抗议校方占用哈雷姆区(黑人区)的土地来修建体操馆的决定,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园抗议活动。激进学生一度占领了学校的办公楼和教室,校方最终不得不动用校外的警察力量来终止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桩发生在他十分钟爱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抗议事件,给霍夫施塔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哥伦比亚大学打破213年的惯例,邀请霍夫施塔特作为教师代表,取代校长为全校毕业生致辞。霍夫施塔特在精心写作的短篇演讲中,对学生占领校园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说他理解学生的立场,并支持学生对越战的反对,但他不能容忍学生对校园的占领,反对激进学生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于整所大学,因为大学“不是一个政治社会,也不是政治社团聚会的中心”。他强调说,大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进行自由探索和批判的中心”,不应该“被政治化”。他虽然意识到在现实政治中一所大学要做到“完全的和纯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但主张“(政治)中立必须成为大学的目标”,因为“学术自由”对于一个社会和文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56]
在《反智主义》中,霍夫施塔特努力批判的是右翼保守派的“反智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威胁。他在书中也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自称为正统文化的反叛者的人根本没有展现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感,他们所表现出的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是一种“反智”现象。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反智主义”会在美国智识生活的中心—大学—出现,而他的学生会加入到校园左翼政治的“反智主义”潮流中去。这不能不引起霍夫施塔特的深思。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大众政治和大众的关系?这个问题早在柯蒂1954年的演讲中就被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柯蒂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自视甚高,以精英自居,甚至远离人民,而应该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那里获得支持。柯蒂引用爱默生的话警告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人民一起前进,他将消失在黑夜之中”(March without the people, and you march into the night)。[57]
对于霍夫施塔特来说,在建构“反智主义”的历史叙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谁是“人民”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过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此刻他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与“人民”,或者与哪一种“人民”站在一起。两年之后,霍夫施塔特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为后人留下异常丰富和卓越的学术遗产。但在此时此刻,他却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面临了一种困境——作为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同时又高度“反智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直到今天,这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不仅依然在美国存在,而且也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演变成为困扰所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问题。
本文原文是作者应邀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写的中文版序(九州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21年版),删节版发表在《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此版为修订后的完整版本。作者感谢后浪出版公司和《美国研究》诸位编辑对原稿的文字润色与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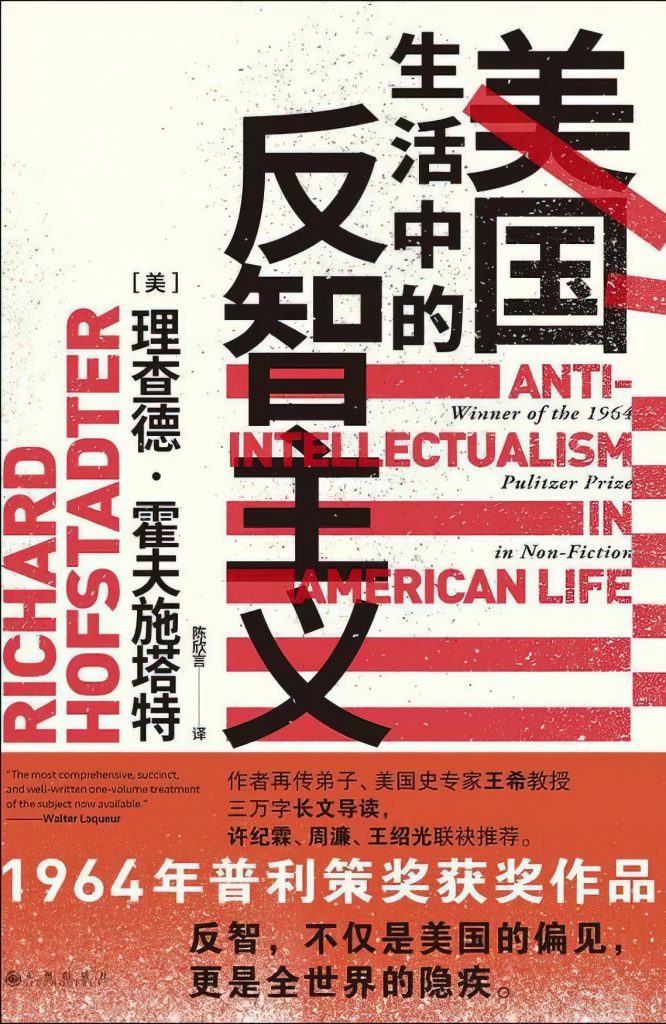
[ 美 ]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陈欣言译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版